| T O P I C R E V I E W |
| Nineveh |
Posted - 11/25/2011 : 15:06:32
小弟新近完成了對英國歷史學家斯蒂文•朗西曼(Steven Runciman)專著《1453,君士坦丁堡陷落》一書的翻譯,并完成了初步校對潤色,正在聯繫出版中。
1453年5月,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攻陷,是世界歷史中的一件大事。尤其是近十年以來,西方關於這一歷史戰役的專著如雨後出筍,大量湧現,成為了歷史研究中的一個熱點。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文的相關著作卻是鳳毛麟角,近20年中,大陸市面可見的中文專著僅有拜占庭史專家陳志強先生1997年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君士坦丁堡陷落記》一書(約10萬字)。此外,中文書籍還包括臺灣三民書局2006年出版的,日本歷史學家鹽野七生《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一書(楊征美譯)。
斯蒂文•朗西曼先生(Steven Runciman,1903-2000年)為英國著名拜占庭史、中世紀史專家。他出生于貴族世家,精通多國語言(英語、拉丁語、希臘語、土耳其語、阿拉伯語、波斯語、敘利亞語、格魯吉亞語、希伯來語、亞美尼亞語),自劍橋三一學院畢業後,周遊列國,于多所大學任教,尤其在拜占庭歷史及十字軍史方面頗有造詣。1965年,斯蒂文《1453,君士坦丁堡陷落》一書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後,迅速成為該領域經典之作,近半個世紀以來,備受推崇,至2008年,已累計重印達16次之多。斯蒂文雖在西方享有盛譽,但該書卻從未譯介至國內。這部作品篇幅適中(約15萬字),結構清晰,風格嚴謹,尤其是旁徵博引,考據入微,令人歎為觀止,可作為國內相關歷史研究者與普通歷史愛好者這一領域的重要參考書。
在這裡開欄貼出譯稿部份內容,供大家交流、指正。
版本資訊:Steven Runciman,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145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65, Canto edition 1990, Sixteenth printing 2008.
目錄
序言
1 垂死的帝國
2 崛起的蘇丹國
3 皇帝與蘇丹
4 西援之殤
5 準備圍攻
6 圍攻開始
7 金角灣失守
8 褪色的希望
9 拜占庭的末日
10 君士坦丁堡陷落
11 被征服者的命運
12 帝國與征服者
13 倖存者
附錄一 關於君士坦丁堡陷落的主要參考資料
附錄二 征服之後的君士坦丁堡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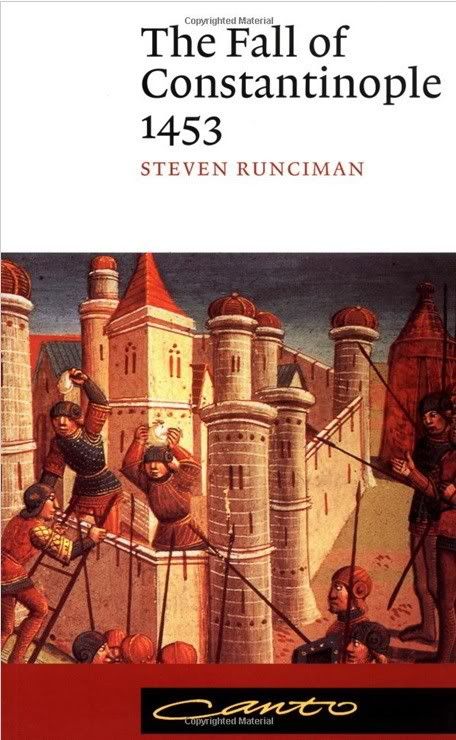
序言
昔日的歷史學家們常常以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作為中世紀結束的標誌。然而今天的人們認為歷史的長河中很難尋找出上述絕對的界限。在陷落發生前很長時間,義大利及整個地中海世界已經興起了我們稱作“文藝復興”的運動。而在1453年之後很久,中世紀的思想依然在北歐盛行著。1453年以前開端的地理大發現已經深遠改變了整個世界經濟,但尚需數十年其影響才能在歐洲充分顯現。拜占庭的滅亡與奧斯曼土耳其的崛起自然與上述變化息息相關,但其影響並非立竿見影,當下立現。拜占庭的知識在文藝復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1453年前半個多世紀,便有相當一部分拜占庭學者來到義大利謀求更好的發展,在這以後,同樣有學者從異教徒的土地,甚至威尼斯治下的前拜占庭島嶼遠赴歐洲“淘金”。奧斯曼實力的增長確實引發了義大利諸多商業城市的擔憂,不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並沒有立即終止東地中海貿易,受到顯著影響的只有義大利至黑海的商業航線。對威尼斯而言,奧斯曼佔據埃及的打擊要劇烈得多,而對熱那亞而言,其在義大利商業霸權的動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要遠大於失去拜占庭商業區的損失。
即使從政治意義上看,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影響也是很有限的。當時奧斯曼人已經抵達多瑙河岸並威脅中歐,任何人都可以看出拜占庭首都難逃一劫——後者領土幾乎萎縮至僅限衰敗不堪的君士坦丁堡一隅,自然難以與佔據了大半巴爾幹和小亞細亞的奧斯曼土耳其抗衡,何況土耳其還擁有那個時代歐洲最強勁的戰爭機器。誠然,君士坦丁堡的失陷對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刺激頗深。不過,那時的西歐諸國並無如此遠見卓識,可以預料到奧斯曼的征服會從此一發不可收拾。他們並未因此顯著改變其“東方政策”,甚至,他們是否具有一貫的“東方政策”都大為可疑。只有教皇或許表現出真正的不安與痛心,並開始策劃反擊,不過很快更加迫在眉睫的危機就會到來了。
看上去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似乎不值得大書特書,不過對兩類人而言,它還是至關重要的。於土耳其人來說,攻佔該城不僅為他們帶來了一座新都,還保證了帝國歐洲部分的安全。君士坦丁堡扼歐亞交界要道,且位於奧斯曼領土中心,若始終掌握在拜占庭異教徒手中,不免令奧斯曼人如鯁在喉。單獨是希臘人固然不值得畏懼,但從君士坦丁堡再次出現一支基督教十字大軍的可能,無疑會成為土耳其人揮之不去的夢魘。直到今天,經歷了歷史的興衰變遷之後,土耳其人依然領有該城,他們在歐洲站穩了腳跟。
對希臘人而言,這一事件甚至更加令人刻骨銘心。這是希臘人一段歷史的終結。燦爛的拜占庭在世界文明舞臺閃爍了千年之久,1453年它雖已衰敗,但尚能苟延殘喘。雖然帝都的人口不斷減少,但君士坦丁堡仍擁有那個時代最優秀的古羅馬希臘學者。上帝的代言人,城中的羅馬皇帝,令每一個希臘人自豪地感到,自己依然是一個偉大東正教國家的一員。此時的皇帝或許對臣民的實際意義甚微,但他依然地位尊貴且是上帝統治的象徵。然而,隨著皇帝與他的城市一同殉難,異教徒的統治開始,希臘人不得不為其生存而苦苦掙扎。所幸希臘文明並未消亡,這無疑源自其文明的內在活力與希臘人的勇氣。
對我而言,君士坦丁堡陷落中的希臘人是一群帶有悲劇色彩的英雄。我的很多前輩對此也深有同感。例如吉本(Edward Gibbon)雖對拜占庭抱有偏見,但也贊許其末日中體現的氣魄。而在愛德溫•皮爾斯(Edwin Pears)60年前出版的專著中,對希臘人的同情與讚譽體現得尤為明顯——雖然某些現代的研究令他的著作顯得略微過時,但因其扎實的考據與淵博學識,此書在今日仍頗值一讀——我本人也深受其影響。當然,在這之後還有相當的學者從事這一領域研究,並取得成果。尤其在19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500周年之際,湧現了大量論文與著作。不過,除去1914年古斯塔夫•施倫貝格爾(Gustave Schlumberger)的專著與皮爾斯的作品,整整半個世紀,西方再沒有關於這段歷史的長篇專著出版。
在試圖填補此項空白的嘗試中,我借鑒了大量近代學者(不論在世或過世的)的相關著作,我將在注釋中一一表達謝意。健在的希臘學者中,我尤其要提到紮基西諾斯(Zakythinos)教授與左拉斯(Zoras)教授。在奧斯曼歷史方面,我要特別感謝巴賓格爾(Franz Babinger)教授,雖然其名作《“征服者”穆罕穆德與他的時代》並未詳細注明參考書目。關於土耳其早期歷史方面,維特克(Wittek)教授的專著對我幫助甚多。土耳其青年學者我則首推İnalcık教授,而吉爾神父(Father Gill)關於佛羅倫斯大公會議的著作也具有相當價值。
我在附錄中簡要談及了本書所用主要參考資料。其中一部分是比較罕見的。基督徒方面的文獻,由德蒂爾(Dethier)教授在80年前統一收錄於《匈牙利歷史文獻》(Monumenta Hungariae Historica)中的兩卷(二十一、二十二兩卷之第一部、第二部)。它們雖然成功付梓,但並未公開出版,且包含不少錯誤。至於穆斯林方面的資料,由於普通讀者閱讀上的困難,更加令人難以親近。我希望我能為讀者們提供其中的精華部分。
若沒有倫敦圖書館,本書將永遠無法完成;我也要對大英博物館閱覽室全體職員的耐心幫助表示感謝。此外我不能不提到帕帕斯塔夫洛(S.J. Papastavrou)先生為本書進行的校對工作,以及劍橋大學出版社理事與職員們的寬容與友善。
關於本書譯名的說明:
我個人無法確保所有源自希臘語、土耳其語的譯名均無懈可擊。對希臘專有名詞我儘量使用我個人認為常見、自然的形式。對土耳其專有名詞我一般採用音譯,除非是現代土耳其語詞匯,後者我則使用現代土耳其語拼寫。我將“征服者”蘇丹的土耳其名稱作Mehemet,而非Mahomet或Mohammed。我希望我的土耳其朋友能原諒我在書中使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一詞而非“伊斯坦布爾”(İstanbul)——因為倘若那樣做,未免有失之迂腐的嫌疑。[1]
注釋:
[1] 從10世紀時起,突厥人和阿拉伯人開始稱君士坦丁堡為“伊斯坦布爾”(İstanbul),這個名稱來自希臘語στην Πόλη,即“在城裡”、“進城去”。1453年土耳其人征服君士坦丁堡後,“伊斯坦布爾”逐漸成為該城的官方名稱,與“君士坦丁堡”一詞並用。土耳其共和國成立後,於 1930年將市正式更名為“伊斯坦布爾”。斯蒂文40年代曾在伊斯坦布爾大學任教,而完成此書時間在1964年,書中所用“君士坦丁堡”舊稱顯得不夠“正式”,故而他做出以上說明。譯注。
|
| 20 L A T E S T R E P L I E S (Newest First) |
| knightdepaix |
Posted - 09/28/2014 : 23:31:15
就朗西曼而言,好奇他如何能對這麽多國語言這麽快入手的? |
| knightdepaix |
Posted - 09/28/2014 : 23:29:43
好書,現在有著名/名星學者作品的中譯本。 |
| Nineveh |
Posted - 09/28/2014 : 22:45:52
書一模一樣,但出版社標註卻不同,不知是怎麼回事????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CN11146944
ps: 最近鳳凰衛視做的兩期節目
http://book.ifeng.com/kaijuanbafenzhong/wendang/detail_2014_09/26/112321_0.shtml
http://book.ifeng.com/kaijuanbafenzhong/wendang/detail_2014_09/28/100013_0.shtml |
| 陸戰屋小步兵 |
Posted - 09/19/2014 : 10:27:18
好書阿,不過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有關東羅馬兵役與軍事制度的專書?
讀書不成先用劍 用劍無它A讀書 讀書用劍兩無成 落魄江湖它W負 |
| Nineveh |
Posted - 09/17/2014 : 13:26:49
關於朗西曼爵士的生平簡介,可參看我翻譯的此文:
斯蒂文朗西曼爵士訃告
作者奈傑爾•克萊夫(Nigel Clive)
《衛報》,2000年11月3日
歷史學家、旅行家、唯美主義者斯蒂文•朗西曼爵士(拜占庭帝國及十字軍權威專家)不幸逝世,享年97歲。他於1951至1954年出版的三卷本《十字軍史》,向我們彰顯了他所主張的“歷史學家應該嘗試記錄那些改變人類命運的重大歷史事件和運動”,也體現出歷史的任務應該是給予對人性的深層次理解。同時他的作品也具有雅俗共賞的特徵。
對朗西曼而言,十字軍是最後一場蠻族入侵;其災難的根源在於他們缺乏對拜占庭的理解。“崇高的理想為貪婪、殘暴所玷污,寬容和進取被盲目狹隘、自以為是所吞沒。聖戰不過是一場打著上帝旗號偏執的戰爭,骨子裡與基督教精神格格不入。”他這樣寫道。
朗西曼是第一代多克斯福德子爵次子,其祖先可上溯至18世紀中期的蘇格蘭畫家亞歷山大•朗西曼。他的父親曾任英國首相阿斯奎斯閣員,母親也是國會議員。令朗西曼慶倖的是,作為次子,他不必被迫從政或繼承家族的船運產業。相反,他早早地便顯露出驚人的語言天分,三歲便能掌握法語,六歲拉丁語,7歲希臘語,11歲俄語……
他曾贏得伊頓公學獎學金,在哪裡開始對拜占庭歷史產生興趣。他知名的同窗包括:西瑞爾•康諾利、喬治•奧威爾以及阿斯奎斯之子,綽號“海鸚”的小阿斯奎斯。
1921年,他前往劍橋三一學院深造。通過以繪有普緒喀與丘比特圖畫的法國壁紙將自己的宿舍妝點一新,斯蒂文初步顯露出某種高雅的唯美主義傾向。通過校友喬治的介紹,他得以與斯特雷奇、J.M.凱恩斯、吳爾夫夫婦等相識,從而同布盧姆斯伯裡團體(Bloomsbury group)有所接觸。
從踏入史學研究一刻起,朗西曼便師從素以脾氣怪異著稱的J. B.布瑞,後者亦是不列顛首位拜占庭學大師。他巧妙地發現了導師喜歡午後散步的習慣,並以此為契機獲得了不少個人輔導。
在一次身患胸膜炎後,醫生建議朗西曼為恢復健康進行一次海上遠行——於是他去s86中國,適逢中國內戰正酣,但這也未能阻止他與末代皇帝溥儀建立友誼,他甚至與後者表演了鋼琴二重奏。
1924年,朗西曼首次來到希臘,並且為希臘小鎮莫内姆瓦夏(Monemvasia)所迷醉,稍後他亦領略了伊斯坦布爾舊城的風光。回到劍橋後,他集中精力編撰自己的論文,並引用了不少當時罕見的亞美尼亞、敘利亞史料,1929年,其科研心血終於成書,即朗西曼的第一部專著《羅曼努斯•利卡潘努斯皇帝》,稍後又出版了《保加利亞第一帝國》與《拜占庭文明》。
朗西曼自1927年開始在三一學院從事教學及研究工作直至1938年。他的第一位學生是蓋•伯吉斯,他對後者的睿智博學與骯髒的指甲記憶猶新。。他的收官弟子是唐納德•尼科,後來成為了倫敦大學現代希臘語及拜占庭史教授。在此期間,他還多次遊歷了耶路撒冷、泰國、希臘、土耳其。
1938年隨著祖父去世,朗西曼(繼承了遺產)經濟上足以放棄劍橋大學職位,他聽從友人建議,離開劍橋,專心於學術創作。二戰期間,他作為使館外交官先後去過索菲亞、開羅及耶路撒冷,最終來到伊斯坦布爾教授拜占庭藝術及歷史達三年之久。這段時光為他追尋昔日十字軍足跡撰寫《十字軍史》打下了基礎,訪問敘利亞期間,他還被授予了回教榮譽“苦修士”頭銜。
二戰結束後,朗西曼欣然接受了指導英國文化協會在希臘工作的任務,在大約兩年的時間裡,他與帕迪•弗莫爾(Paddy Leigh Fermor)、 雷克斯•沃納(Rex Warner)通力合作,建立了深厚情誼,並贏得了雅典人的愛戴。他還與希臘外交官喬治•塞菲裡斯(喬治•塞菲裡斯後來以詩人身份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私交甚篤。閒暇時間,朗西曼則專注於收集各種聖象、雕塑及愛德華•李爾的畫作。
1947年,朗西曼出版了之前甚少有人涉獵的《中世紀的摩尼教》一書,隨後回到不列顛開始中世紀史的寫作,他深居簡出,交替居住於倫敦家中與父親1926年買下的小島伊格(Eigg)。1951至1967年,他還擔任盎格魯-希臘聯合會(Anglo-Hellenic League)主席職務。
1951至1954年陸續出版的三卷《十字軍史》為他奠定了崇高學術聲望。評論家對他高超的歷史敘事手法讚歎不已,甚至把他與19世紀著名英國歷史學家麥考利相提並論。
《東方教會大分裂》出版於1955年,《西西里晚禱》出版於1958年。同年朗西曼被授予騎士頭銜,3年後他得到了希臘政府頒發的鳳凰勳章(為第二等級,大司令勳章,knight commander of the Greek Order of the Phoenix)。作為他多年對拜占庭史關注的成果,1965年出版了《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1968年出版了《囹圄中的偉大教會》,1970年《最後的拜占庭文藝復興》,1972年《東正教會與世俗社會》,1975年《拜占庭風格與文明》。
在希臘米斯特拉,甚至有一條街道以朗西曼命名,他特意於1980年出版的關於米斯特拉的著作中對此表達了謝意。
雖然朗西曼本身並不是東正教徒,但他一直對東正教抱有好感,並堅信它才能代表基督教的未來。
1966年伊格島被出售後,他遷居至鄧弗裡斯郡(Dumfrieshire)附近的艾爾希希茲居住。在他漫長而逍遙的一生中,朗西曼始終堅信自己的根在蘇格蘭。這是他最後的居所,在這裡他高朋滿座,而朗西曼也不忘向友人們展示他的藏品:從18、19世紀音樂盒、水煙袋到各式念珠,從亞歷山大•朗西曼到愛德華•李爾,從打油詩到水彩畫……在他80歲時,收到了一份殊榮——英國名譽勳位(Order of the Companions of Honour,簡稱CH)
雖然他定居蘇格蘭,只是偶爾造訪倫敦,斯蒂文依然抽出時間赴國外演講及研究科普特教會。1987年,隨著第四頻道播出一期製作精良的關於他的訪談節目《斯蒂文•朗西曼爵士:通往東方的橋樑》,他的名氣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即使斯蒂文已經80多歲高齡,他依然保持了驚人活力與智慧,並且令他各個年齡層的朋友著迷。1991年,蘇格蘭國家畫廊展出了斯蒂文收藏的李爾水彩畫,每幅作品均附有他的簡介與評論,一同展出的還包括蘇格蘭畫家斯蒂芬•康諾伊(Stephen Conroy)為他創作的肖像畫照片。不久後,斯蒂文出版了《旅行家字母表》,書中用26個字母的形式回顧著他一生閃耀的旅行記憶,A代表雅典,Z代表錫安(Zion,一般用作耶路撒冷的別稱)。
1992年,朗西曼重新發現了他1935年創作,名為《複樂園》(與彌爾頓的長詩《複樂園》同名)的小說。小說講述了一次前往伊拉克庫爾德斯坦的探險,風格一如既往地體現出斯蒂文式的睿智和幽默,並注明獻與喬治•賴蘭茲(George Rylands,英國文學學者及戲劇導演,長期供職于劍橋國王學院,為世界頂級莎士比亞專家,與斯蒂文是伊頓公學同窗)。這部小說僅僅少量印刷,並用來替代聖誕卡送給他的親朋好友。
1993年,為了慶祝朗西曼的90歲生日,其伊頓公學昔日同窗、英國拜占庭學同好及劍橋三一學院共同為他舉辦了生日宴會。劍橋大學出版社亦為他舉辦了招待會,而蘇格蘭國民信託(the National Trust for Scotland,致力於蘇格蘭自然及歷史文化保護的組織)則贈給他一所位於艾爾郡的公寓的使用權。最終,他邀請了數百位故交摯友參加在他家中舉辦的生日宴。
在此期間,朗西曼依然堅持旅行。1994年他遠赴希臘利姆諾斯島參加了“愛琴海宣言”的發佈儀式(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希臘文化部共同宣導的將希臘群島打造為歐洲文化公園的項目)。1995年四月,作為“阿索斯山之友”的主席,他在《時代》雜誌撰文哀歎曾經超越種族、延續千年的傳統信仰,如今已遭遇了危機。
1997年底,在定期造訪巴林、希臘以外,朗西曼發表了一篇關於風華絕代的瓦拉幾亞公主瑪爾特•比貝斯科(Marthe Bibesco,1886-1973,羅馬尼亞作家)的評論。同年,在雅典他從希臘總統手中接過了國際文化獎金(由奧納西斯基金設立),他將全部獎金(約合125000美元)捐給了阿索斯聖山。
朗西曼對科索沃戰爭感到甚為痛心,他尤其同情塞爾維亞人的遭遇。在他90歲高齡後,開始撰寫自己的回憶錄。朗西曼終生未娶。
詹姆士•科克倫•斯蒂文森•朗西曼(James Cochran Stevenson Runciman),歷史學家,唯美主義者,旅行家,生於1903年7月7日,卒於2000年11月1日。
|
| dasha |
Posted - 09/17/2014 : 13:11:50
小弟考慮的其實是台灣某些賣大陸書的店,或者是盜版大陸書的出版社,不知道動作會多快...... |
| Nineveh |
Posted - 09/17/2014 : 13:07:19
quote:
Originally posted by dasha
終於出版......恭喜了!台灣要買的話......
大陸的亞馬遜網站和淘寶應該可以直接送貨到台灣。
http://www.amazon.cn/3/dp/B00MWJ6TMU/ref=zg_bs_661363051_4
說起來最早對這個選題感興趣還是很久以前在MDC看到的一篇文。 |
| dasha |
Posted - 09/17/2014 : 07:59:24
終於出版......恭喜了!台灣要買的話...... |
| Nineveh |
Posted - 09/16/2014 : 09:19:03
此書已經由北京華文書局在今年8月正式出版。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5899496/
http://www.readit.com.cn/xstj/2014/09/183852.shtml

|
| Nineveh |
Posted - 12/13/2011 : 22:00:32
正在聯繫出版。如果一切順利,明年能見到。這也應該是斯蒂文先生的著作第一次翻譯成中文。 |
| fatisuya |
Posted - 12/03/2011 : 20:34:36
喔,這本推出記得告知,小弟一定敗一本。^^ |
| dasha |
Posted - 11/29/2011 : 11:04:35
帝國從失去埃及後就停止給首都公民發糧的義務,同時也因為失去巴勒斯坦與埃及,喪失了很重要的精密工藝品與糧食的生產地,經濟就只能靠通商賺過路費,威尼斯之類城邦的崛起,其實也就是砍掉拜占廷收入的一個重要因素.然後,俄羅斯商路的出現,多了一個完全無法受控於拜占庭的管道,對拜占廷更是打擊.
十世紀時回教帝國的貴金屬礦漸趨枯竭,也與三世紀羅馬帝國境內貴金屬礦漸趨缺乏一樣,對商人與商業都有持續性的重大影響.於是,拜占庭就缺錢發餉了...... |
| n/a |
Posted - 11/28/2011 : 21:12:20
其實換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歷史往往會有不同的認識,起初拜占庭對西歐十字軍表現出曖昧甚至是支持的態度,是因為拜占庭認為這幫免錢的雇傭兵可以幫他們收拾掉逐漸成為威脅的賽爾柱土耳其勢力。
但是等到第一次十字軍殺開一條血路、幫助拜占庭奪回幾座小亞細亞的失地要前往中東之際,拜占庭卻開始擔憂十字軍對於阿拉伯人的打擊將會危害到拜占庭與阿拉伯世界間的邦交,使得他們失去一個從背後克制塞爾柱的幫手,於是採取了斷糧斷援希望令十字軍知難而退的處置方式。
站在拜占庭的立場幫十字軍走到半路也已經是仁至義盡;但站在第一次十字軍的立場來看這簡直就像把他們帶去荒野裡然後棄之不顧一般,不難想像十字軍參與者們對於拜占庭這個"盟友"會怎麼想。更要命的是這支十字軍最後還是千辛萬苦地走到了目的地、攻陷了耶路撒冷。結果演變成拜占庭同時得罪了十字軍、阿拉伯和土耳其,搞到自己腹背受敵裡外不是人的慘狀。
在我來看拜占庭的歷史就是小聰明搞太多結果把自己害死的歷史,他們老是打著請人助陣不付薪水的如意算盤,或是以夷制夷過河抽板,拜占庭的外交政策就是天底下沒有永遠的盟友;但拜占庭撐了太久的後果是,這個政策使他們失去了所有的盟友。
熱內亞在13世紀初幫助土耳其一方是完全有理由的,這是因為他們在第四次十字軍戰爭時被威尼斯人逐出了君士坦丁堡之故。然而,倘若要追究起來,如果不是威尼斯人在1170年被拜占庭與熱內亞聯手逐出,那麼威尼斯也沒必要大費周章籌組一支總勢八萬人的遠征軍跑去襲擊君士坦丁堡來贏得商業特權。威尼斯人在君士坦丁堡的特權早在10世紀末奧賽羅協助巴西爾二世勦滅海賊之後便已經被帝國官方認可,但是2個世紀後拜占庭的財政終於窘困不堪到他們必須食言收回這種貿易特權為止---其結果就是十字軍的燒殺擄掠。
而加特蘭軍團的問題在於拜占廷從來沒給足他們夠餉,而不是因為他們的狼子野心想要叛變---倘若雇主給的薪水足,那誰想冒著生命危險舉起反旗呢。
拜占庭帝國末期的財政破滅,處於一種挖東牆補西牆的困境中,他們出賣威尼斯人來討好熱內亞、偶而也驅逐熱內亞人張手歡迎威尼斯;擄人勒贖、敲詐、借貸與貿易稅成為帝國財政上最大的收入,但他們自己卻連一支像樣的海軍都拼湊不出來,十四世紀末的東帝國水師已經只剩下一對手指頭艘數的戰船,有沒有水兵可以服役執勤也頗為可疑,陸上領土的淪陷逼迫拜占庭得砸錢湊出一支陸軍或是請來一支夠基數的陸上傭兵保衛疆域,但是排擠了海軍預算的結果是令帝國被加速與它的海外領土切斷,且在海權上更仰賴西歐拉丁人的奧援而喪失自主性。同時發餉有一陣沒一陣的陸軍,別說是雇傭兵,就算是希臘本地的部隊忠誠度也都值得懷疑。
From this day to the ending of the world、
從今天開始直到世界末日,
But we in it shall be remembered;
我們永遠會被記住。
We few、we happy few、
我們這一小撮,幸運的一小撮,
we band of sisters;
我們是一群緊緊相依的姐妹。
For she to-day that sheds her blood with me
誰今天與我一起浴血奮戰,
Shall be my sister.
誰就是我的姐妹。 |
| LUMBER |
Posted - 11/27/2011 : 15:45:44
風雲變化的拜占庭跟土耳期局勢....結果顯得最愚蠢的莫過於西方來的十字軍.
熱那亞幫助土耳其人渡海也是一絕.... |
| Nineveh |
Posted - 11/27/2011 : 11:16:45
quote:
Originally posted by LE323
當出拜占庭皇帝沒出錢買砲真是可惜了
如果我是他拼死也會湊錢去買
就算沒錢買不起也要把烏爾班抓起來殺了
這種軍事技術無論如何也不能讓自己敵人得到
君士坦丁確實過於宅心仁厚。不僅是烏爾班,他將自己心懷異志且親近土耳其的兄弟德米圖斯冊封為摩里亞專制君主,也是一記昏招。應該將這兄弟嚴密控制起來。按照蘇丹的做法,兄弟們一概處死,就更沒有禍起蕭牆的顧慮了。 |
| LE323 |
Posted - 11/26/2011 : 18:03:30
當出拜占庭皇帝沒出錢買砲真是可惜了
如果我是他拼死也會湊錢去買
就算沒錢買不起也要把烏爾班抓起來殺了
這種軍事技術無論如何也不能讓自己敵人得到 |
| Nineveh |
Posted - 11/25/2011 : 23:37:20
quote:
Originally posted by kelly_ts_devon
補充一下:
鹽野七生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三民出版的,敝人在2006以前就看過了.也許是版次不同的關係吧.
1999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2006年第二次印刷。我手上的是2006年那次。 |
| kelly_ts_devon |
Posted - 11/25/2011 : 20:21:29
補充一下:
鹽野七生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三民出版的,敝人在2006以前就看過了.也許是版次不同的關係吧. |
| Nineveh |
Posted - 11/25/2011 : 15:12:32
第二章 崛起的蘇丹國
歷史上強大的拜占庭往往離不開安納托利亞(Anatolia)。這塊巨大的半島,昔日也被稱作小亞細亞,在羅馬時代一度是世界最繁榮的地區之一。伴隨著羅馬帝國的衰落,瘟疫疾病的橫行以及波斯、阿拉伯人于西元7-8世紀的入侵,這一地區因此大傷元氣。不過到了9世紀,安納托利亞恢復了安定。一條精心組織的防線隔絕了敵人的進犯。農業回復了生氣,並在君士坦丁堡等城市中找到了市場。西部河谷地區到處是橄欖、果樹與穀物,山區則牛羊成群,而在灌溉系統完善的地區,則是沃野千里的景象。皇帝的政策是抑制地產兼併,維護自由農的權益,小亞細亞的農民很多屬於軍區農兵,平時務農,戰時從軍。中央政府通過頻繁的視察及給予地方長官優厚俸祿,維持著對這一地區的掌控。
小亞細亞的繁榮取決於一條穩定的前線。它的防務採取了一種特殊的方式。邊境守備被委任給若干邊區“男爵”(baron)負責,而這只軍隊被稱作“邊防軍”(Akritai,希臘語中的原意是邊境,後來引申出邊防軍之意。譯注)。他們主要的職責有二:擊退外敵對邊境的侵襲,主動襲擾敵人的土地。這群軍人無法無天,喜歡自由行事,厭惡一切政府對他們的干預,拒絕交稅,同時總是要求為其軍功得到賞金。除去亞美尼亞人的土地,邊境地區大多是人跡罕至的,這些戰士為了生存往往敢於鋌而走險。不論拜占庭與阿拉伯國家是戰是和,邊境衝突一直持續不斷。這倒並非是邊防軍們窮兵黷武或者對敵方守軍懷著刻骨仇恨——不如說這是他們的生活方式。雖然穆斯林邊防軍宗教上相對狂熱,但這也並未阻止雙方友好往來甚至互相通婚。兩方都有不少“異端”信徒。拜占庭邊防軍士兵多數屬於獨立的亞美尼亞教會,樂於庇護所謂的異教徒;對面的穆斯林軍官對此同樣心有戚戚。
然而平衡隨著哈裡發的式微與拜占庭的擴張而被打破了。10世紀中期拜占庭在東方取得了一系列輝煌勝利,收復了大片領土,兵鋒一度抵達敘利亞。新的邊境線不再是荒涼的山區,而是富饒的平原。新的防線主要依靠駐紮在安條克等城市的正規軍負責,傳統的安納托利亞邊防軍已經過時了。前邊防軍們轉而利用帝國開疆擴土的時機,在東安納托利亞收穫了大量地產。這些男爵們雖然以農耕為生,不過依然桀驁不馴,甚至雇傭私人軍隊保衛自己的莊園(而這些軍人往往是昔日的自由農)。這些新型的大地產貴族割據一方,在11世紀中期逐漸成為拜占庭政府心頭之患。另一方面,拜占庭盲目擴張也存在隱憂,它吞併了亞美尼亞王國(這個古老的基督教國家過去一直作為拜占庭與東方異教徒國家之間的緩衝國),並用其貪得無厭的稅吏及東正教會令亞美尼亞人心生憤懣(亞美尼亞教會教義與東正教不同,譯注)。這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帝國東部的防禦。
很快,往日的一些帝國盟友就會成為東部的心腹之患。幾個世紀以來,突厥人一直從突厥斯坦四處遷移,尋求新的牧場。早在西元6世紀,拜占庭便與之在中亞及俄羅斯大草原發生了接觸。這一部突厥人稱作可薩人(Khazars),他們建立了自己的國家,其王公還曾與拜占庭王室通婚——雖然偶爾也兵戎相見,不過多數情況下都是拜占庭的盟友,以及重要的雇傭兵源。而這些突厥傭兵很多都在帝國境內(尤其在安納托利亞)永久定居下來,其中一部分甚至皈依了基督教。突厥人的另一部,即烏古斯人(Oghuz Turks),則自波斯向阿拉伯帝國境內遷徙,他們同樣為阿拉伯哈裡發充當傭兵,並皈依為穆斯林。隨著哈裡發勢力的衰落,這些昔日的部將漸漸崛起。穆斯林突厥人于963年建立了伽色尼王朝(the Ghaznavids,963-1168,都城在今阿富汗Ghazni),當偉大的穆罕穆德蘇丹(Mahmud of Ghazni,971-1030)在位時,國力最為鼎盛,其疆域包括今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及北印度一部。不過好景不長,穆罕穆德去世後,霸權轉入了統領烏古斯人的塞爾柱(Seljuk)家族手中。塞爾柱的後人們獲得了整個伊斯蘭世界突厥人的領導權。1055年,偉大的圖格魯爾貝伊(Tugrul Bey)迫使阿巴斯王朝(即黑衣大食。譯注)哈裡發授予其正統伊斯蘭保護者的身份(即迫使哈裡發承認其為蘇丹),其領土包括波斯、呼羅珊及若干附屬國,塞爾柱王朝真正建立起來了。
巴格達的哈裡發央求塞爾柱人的保護是為了防備以埃及為中心的法蒂瑪王朝(即綠衣大食,譯注),後者的勢力已經擴張至敘利亞。法蒂瑪王朝與拜占庭關係親密,塞爾柱人深恐東羅馬在其背後進攻,從而令塞爾柱蘇丹國與阿巴斯王朝腹背受敵。的確,不少突厥王公早已移居至拜占庭境內,並作為邊疆男爵為帝國效力,他們磨刀霍霍,只待時機一到便可對敵境發動襲擾。圖格魯爾貝伊的繼任者,其侄子阿爾普•阿斯蘭(Alp Arslan)決心一勞永逸地剪除西面拜占庭的後患。他首先攻佔並劫掠了前亞美尼亞王國首都阿尼(Ani),並鼓動其邊防軍們主動出擊。[1]拜占庭人雖然吞併了亞美尼亞,但是卻沒有足夠的兵力來守衛它。此時,軍區已經解體,安納托利亞邊防軍幾乎蕩然無存。面對如此嚴峻的局面,1071年,拜占庭皇帝羅曼努斯四世決定御駕親征以解除邊境的危機。不過由於帝國財政大不如昔,軍隊的品質規模都降低了,其主力已淪為雇傭軍,既有來自西方的歐洲人,也有來自東方的庫曼突厥人(欽察人一支)。阿爾普•阿斯蘭此時正與法蒂瑪王朝交戰,他將拜占庭的行動看做拜占庭-法蒂瑪軍事同盟的陰謀,於是立即回師去面對新的勁敵。
1071年8月19日(星期五),著名的曼特齊克戰役爆發了。羅曼努斯皇帝英勇有餘,而智謀不足,其雇傭軍的忠誠度也很不可靠。戰役的結果是拜占庭軍隊慘敗,皇帝本人做了蘇丹的階下囚。 (當時拜占庭的軍事實力依然強於塞爾柱突厥人,但是羅曼努斯登基不久,立足未穩,國內權貴並不團結,戰時部隊的嘩變是其戰敗的重要因素,譯注。)
阿爾普•阿斯蘭的目的只是為了保障後方的安全,拜占庭的威脅剷除後,他並不乘勝追擊,而是見好就收,率主力回到了敘利亞。但他留下的邊防軍卻有不同的打算。曼特齊克會戰後,拜占庭的東方防線已經支離破碎,而君士坦丁堡此刻正忙於內鬥,無力重整軍備。即使殘存的少數拜占庭邊防軍(多半為亞美尼亞人)也與首都中斷了聯繫,他們不得不退守於一些孤立的要塞中。土耳其王公們加緊了對拜占庭的蠶食,既然遭到的抵抗如此輕微,他們索性永久佔領了新征服的肥沃土地,並將突厥牧民移民至這裡。
穆斯林的邊區領主常常被稱作“加齊”(Ghazi,來自阿拉伯語,願意為“攻擊”,後來代指“勇士”,譯注),大致相當於西方的“騎士”。他們被授予某種貴族紋章,對君主宣誓效忠(通常是對哈裡發),並且遵守Futuwwa規範[2]。土耳其加齊們本質上是一群武夫,對於組建有效的行政機構興趣全無。他們按照以往的方式統治新獲得的領土,對當地居民幾乎是無為而治,民眾們也樂於與之合作以保證自身安全。而加齊們則主要依靠戰爭的戰利品維持生活。在安納托利亞邊疆區,類似的生活方式已經持續了數百年,因此新的統治者甚少激起臣民的怨懟。誠然,突厥人的湧入也引發了一部分基督徒的逃難人潮,不過,該地區的人口早已魚龍混雜,土耳其人的征服並未導致決定性的變化。然而,隨著土耳其人入侵的深入,情形發生了改變。在一些地區,基督徒於敵軍到來前便已望風而逃,留下了大片無人地區等待突厥移民來填補。一些保有人口的市鎮,雖然極力試圖維持以往的生活方式,卻不得不向征服者屈服。入侵的後果是整個安納托利亞的交通網陷入癱瘓,水利系統、農耕系統殘破不堪,以往的生活方式再也無法繼續了。
由於未遭到有組織抵抗,加齊勇士們在小亞細亞所向披靡,拜占庭的領土龜縮至沿海幾個地區。直到阿萊克修斯一世(Alexios I Komnenos,1081-1118年在位)統治時期,帝國終於重整旗鼓,軍隊戰鬥力得到了回復,加之皇帝善於運用外交手腕在安納托利亞的加齊中挑撥離間[3],帝國終於大體恢復了在小亞細亞的統治。而此時,塞爾柱人受拜占庭的戰爭與謀略困擾,加之第一次十字軍兵鋒銳利,不得不採取守勢。至12世紀初,拜占庭人大體佔據了小亞細亞西部平原及北部、南部沿海地區。土耳其人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安納托利亞中部的土庫曼達尼什曼德王朝以及帝國東部,暫時無力與拜占庭一較短長了。
12世紀末期拜占庭持續衰落,而第四次十字軍的背信棄義給了它最沉重的打擊[4],塞爾柱人抓住這千載難逢的良機,開始大肆擴張。在13世紀上半葉,最強盛的突厥人國家為羅姆蘇丹國(Sultans of Rum),他們與小亞細亞西部的拜占庭流亡政府(即尼西亞帝國)大體維持著良好關係,同時對東方諸國也無覬覦之心。羅姆蘇丹國並不窮兵黷武,而是潛心於以首都科尼亞為中心,治理自己的領土。他們鼓勵商業貿易,資助學術,修復交通網,在其管理下,都市生活又繁榮起來,因其統治溫和而睿智,安納托利亞的基督徒越來越多地皈依為穆斯林,而這一過程是相當平和的。
好景不長,塞爾柱人的盛世被蒙古人終結了。起初,一些躲避蒙古兵鋒的土耳其部落進入小亞細亞,他們在塞爾柱人的西部邊境定居下來,並加入了其邊防軍。1243年,蒙古軍隊出現,旋即決定性地擊敗了羅姆蘇丹國,後者再也未能恢復元氣,淪為了蒙古人的附庸。不到一個世紀,這一曾經顯赫的王朝便從歷史舞臺銷聲匿跡。(1307年,羅姆蘇丹國徹底敗亡,譯注。)
羅姆蘇丹國的式微卻給邊區加齊們提供了大展宏圖的機會,在蒙古人的壓迫下,越來越多的難民加入了他們,其中也不乏前帝國官員、酋長和僧侶,在生存壓力與宗教狂熱的驅使下,他們發起了對西方基督徒新一輪進攻。起初,尼西亞帝國還能應對自如,因為這一拜占庭流亡政權勵精圖治,成功恢復了軍區和邊防軍。但隨著帝國偶然地於1261年收復了君士坦丁堡——雖然這本身值得驕傲,卻為防務帶來了不利後果。帝國要守住西方的領土,就不得不一邊與巴爾幹諸國作戰,一邊防備拉丁帝國餘孽捲土重來。於是,大批帝國軍隊調往西部,而導致東部防禦的空虛。同時,為了應付新的戰事,稅率也普遍提高了,而邊防軍則發現自己的待遇每況愈下。13世紀的最後三十年,一些加齊成功的穿透了拜占庭帝國東部防線。大批受宗教狂熱鼓動、渴望戰利品的突厥人湧向小亞細亞西部。帝國的反擊則時斷時續,軟弱無力。一部分敢於冒險的加齊,例如門特瑟(Menteshe)及艾丁(Aydin)的王公,甚至發動了水陸兩栖攻擊。拜占庭的海軍同陸軍一樣虛弱,於是,不僅安納托利亞西部大片陸地,甚至若干島嶼都被突厥人奪取了。至1300年,拜占庭亞洲部分領土已經萎縮至西部一隅及若干孤立的海港,小亞細亞幾乎完全落入突厥人之手。
在這場變故中,位於安納托利亞西南的門特瑟(Menteshe)酋長國本來處於領導地位。然而,隨著醫院騎士團奪取了羅德島並建立了自己的統治,該公國旋即一蹶不振。霸權隨後轉至臨近的艾丁埃米爾手中,後者是小亞細亞各突厥諸侯中第一個入侵至拜占庭愛琴海附近歐洲領土的。不過艾丁的興起也促成了威尼斯、賽普勒斯與醫院騎士團的聯合。艾丁的北部是薩拉克汗(Sarakhan)諸王公的勢力,其首府位於前尼西亞帝國陪都馬尼薩(Manisa).在特洛伊平原則有卡拉西(Karasi)酋長國,黑海之濱則是切列比(Chelebi)加齊的領地(首府在錫諾普)。位於內陸的若干小國中也有兩個相對的強者,即卡拉曼酋長國與格米延(Germiyan)酋長國,兩者皆以塞爾柱帝國繼承人自居,並建立了卓有成效的統治。卡拉曼於1327年攻佔了科尼亞,由於其領土遠離前線,因此有餘力降服周邊割據的諸侯。而格米延王公也不再滿足于加齊的稱號,極力建立對周邊加齊們的霸權。兩者的努力大體是成功的,不過愛琴海沿岸各酋長國與拜占庭帝國邊防軍們並未實際承認其宗主權。
13世紀後半頁,一個新興的國家在比提尼亞(Bithynian,為古羅馬小亞細亞西北部行省)出現了。它的創始人埃爾托格魯爾(Ertughrul)卒於1281年[5],其繼任者為著名的奧斯曼(Osman)——即奧斯曼帝國創始人。奧斯曼家族的起源問題眾說紛紜,一些在奧斯曼帝國興盛之後流傳下來的材料頗多附會阿諛之處,例如,有記載聲稱奧斯曼人的21世祖先為《聖經》中的先知諾亞,隨後為了提高這份年表的可信度,其祖先又被增加至52世。一份世系表則列入了烏古斯土耳其人的同名祖先——烏古斯可汗,包括他的兒子阿爾普(Gök Alp)及孫子恰伍德爾(Chavuldur)。而據某種傳說,奧斯曼人被認為是烏古斯的第二十四代後裔(也有一種說法,奧斯曼為烏古斯支系後裔)。不過,雖然至13世紀晚期奧斯曼人成功地將部分烏古斯族人納入自己的統治階層,但他們與後者從族源看相去甚遠,甚至後者最初對土耳其人的領導尚懷有敵意。15世紀的一些宮廷弄臣竟宣揚奧斯曼王族乃先知穆聖的後裔——奧斯曼王族都恥於編造此說,因為穆罕穆德的後裔譜系幾乎是眾所皆知的。“征服者”穆罕穆德二世蘇丹,為了同時取悅自己的土耳其與希臘臣民,於是便支持以下理論:他的家族為某個科穆甯王族後裔,其祖先移居至科尼亞(Konya)後,在那裡皈依了伊斯蘭教並迎娶了一位塞爾柱公主。[6]
上述理論均難以得到確鑿證據的支撐。一位審慎的歷史學家,只能總結說:埃爾托格魯爾並非部族首領,而是一位幹練但出身不明的加齊指揮官,出於某種原因,他來到邊區,依靠自身英勇吸引了大批追隨者,並建立了自己的酋長國。而他主要的財富就是他所征服的土地。一塊加齊領地的生存往往是建立在掠奪異教徒領土基礎上的。然而在13世紀末期,大部分穆斯林加齊都已經擴張至小亞細亞的極限——拜占庭的勢力消退了,而海洋阻隔了穆斯林進一步的擴張。雖然一些野心勃勃的海盜,如艾丁與錫諾普(Sinope)的埃米爾,擁有艦隊可以對愛琴海對岸展開襲擾,然而其海軍實力畢竟也沒有強悍到可以開展大規模跨海殖民的程度。在奧斯曼人的土地附近,只有北面黑海之濱的特拉布宗王國可算作一個異教徒王國。加齊領袖們渴望掠奪富庶的土地,回教僧侶與學者們想要逃離可怕的蒙古人,而普通農民同樣期望土地以安居樂業,奧斯曼突然發現自己的小公國已經難以滿足上述人等的需要了。
好在奧斯曼用他的才華解決了這一難題。他的具體措施,今天我們知之甚少。現存於布爾薩清真寺的一塊奧爾汗(奧斯曼之子)遺留的石碑對其父評價甚高——它首次賦予了一位奧斯曼統治者“蘇丹”的頭銜。(石碑上對奧斯曼的稱呼為:Sultan, son of the Sultan of the Ghazis, Ghazis, son of Ghazis, Margrave of the horizons, hero of the world.)奧斯曼作為一個政治強人建立了其權威,同時期的埃米爾們往往忙於自相殘殺,而他卻懂得拉攏人心,贈與歸順他的人加齊頭銜。
拜占庭不可能忽視這些威脅。帝國主動放棄大片領地,並將部隊撤往歐洲看上去是很明智的,因為拜占庭占壓倒優勢的海軍足以保護帝國歐洲部分免遭奧斯曼人的侵襲。 拜占庭人一廂情願地以為,如此奧斯曼人的勢力便會得到抑制甚至分崩離析了。然而事態並未如預料般發展。起初,拜占庭對奧斯曼缺乏重視,在13世紀最後10年裡忙於應付艾丁或馬尼薩等酋長國的進攻。直到1301年,奧斯曼人于科尤爾希薩爾(koyunhisar,亦稱Baphaeum)擊敗了拜占庭人並開始向奧林匹亞山[7]以北移民,這才引起了拜占庭的警覺。拜占庭此時在小亞細亞領土僅剩西北一隅(大致相當於比提尼亞行省),奧斯曼人對這一地區的侵犯是無法容忍的(何況該省份正好位於首都對岸)。但是,拜占庭人的防禦淩亂無章,缺乏成效。1305年,拜占庭皇帝安德羅尼庫斯二世雇傭的加泰羅尼亞軍團在洛伊克(Leuke)附近擊敗了奧斯曼人,但是該雇傭軍很快掀起了叛亂並使帝國陷入長達十年的內戰。內戰期間,奧斯曼軍隊時而為皇帝賣命,時而為加泰羅尼亞軍團效力,並借機擴張自身勢力,直達馬拉馬拉海。1308年,奧斯曼人成功奪取了小亞細亞西部最後一座大城——以弗所(但轉交與艾丁埃米爾),隨後,又奪取了拜占庭在黑海沿岸從伊內博盧(İnebolu)至珊伽裡烏斯(Sangarius ) 的若干市鎮。
加泰羅尼亞軍團叛亂與拜占庭皇室內戰接踵而至,很快,奧斯曼人面臨的威脅解除了。於是奧斯曼人乘機攻城掠地。他們的部隊大部為騎兵,缺乏攻城設備,因此攻城的方式一般為驅逐市郊人口並長期圍困直至城市投降。奧斯曼集中全力圍攻拜占庭比提尼亞行省首府布爾薩(Bursa)。該城坐落在奧林匹斯山腳,地勢險要,城牆堅固,雖然周邊地區紛紛淪陷,但在拜占庭的海上支援下依然堅持了近10年之久,最終彈盡糧絕,於1326年4月6日開城投降。不過此時的奧斯曼已經垂垂老矣,不久便撒手人寰(該年11月)。但他成功的將自己的國家從一個小小的酋長國變為了安納托利亞舉世矚目的強權。
奧斯曼的長子奧爾汗(Orhan)成功繼承了王位。按照昔日傳統,他的兄弟阿拉丁(Ala ed-Din)理應獲得一塊封地,然而後者為了維護國家統一大度地放棄了這一權利。頗受觸動的奧爾汗授予了阿拉丁首相頭銜,令其協助自己處理政務,後者出色地完成了這一使命。(阿拉丁幫助奧爾汗建立了一支職業常備軍,這也是日後土耳其新軍的雛形,譯注。)奧爾汗與父親一樣,作為加齊領袖,也熱衷於奪取異教徒的領地。1329年,經過長期圍困,奧爾汗攻佔了歷史名城尼西亞(Nicaea)。拜占庭皇帝安德羅尼庫斯三世與約翰•坎塔庫震努斯也曾經試圖收復該城,然而戰事陷入了僵局而部隊漸生不滿,同時帝國內部爆發了叛亂,這一計畫不得不終止。接下來輪到了重要的港口城市尼科米底亞(Nicomedia),它在得到海上補給的情形下堅持了9年,然而隨著海上通路被奧斯曼人封鎖,1337年它也陷落了。以尼科米底亞為據點,奧斯曼人大肆擴張,疆域一直達到了博斯普魯斯海峽。
1341年,拜占庭皇帝安德羅尼庫斯三世去世,隨即爆發了攝政約翰•坎塔庫震努斯(John Cantacuzenus)與新皇約翰五世之間的內戰(史稱“兩約翰之戰”),雪上加霜的是,塞爾維亞王國在國王斯蒂芬•杜尚的率領下,也頻頻侵邊騷擾。長期以來,拜占庭雇傭各部落突厥士兵作為軍隊主力,雖然其有酷愛劫掠的陋習。相較而言,奧爾汗的軍隊是最為軍紀嚴明,戰力強悍的。當約翰五世雇傭馬尼薩等地土耳其人時,坎塔庫震努斯則于1344年向奧爾汗求援。後者派去了6000名士兵,條件是要求迎娶坎塔庫震努斯之女。坎塔庫震努斯在內戰第一階段取勝後,繼續雇傭奧斯曼人以對抗塞爾維亞王國(後者一度佔領了帝國第二大城市塞薩洛尼基,譯注)。這場內戰的後果之一便是大量的土耳其人從此在色雷斯一帶定居下來了。
當坎塔庫震努斯於1355年被迫下臺時 ,奧爾汗獲得了藉口進一步入侵歐洲。1356年其子蘇萊曼帕夏率領大軍橫渡達達尼爾海峽,攻佔了喬爾盧(Chorlu)及狄迪蒙特喬(Didymoteicho),從而打開了通往阿德里安堡(今土耳其埃爾迪內)的門戶。奧爾汗不僅攻城掠地,還將大量土庫曼遊牧民移民至新征服的土地上,使色雷斯開始突厥化。當奧爾汗大約於1362年去世時,土耳其人儼然已成為整個西色雷斯的主宰。奧斯曼人在亞洲也頗有收穫,不過其新領土多數是通過和平手段得到的。薩拉克汗與卡拉西兩個酋長國被吞併了,趁著格米延勢力的衰退,奧斯曼人還成功地在埃斯基謝希爾與安卡拉建立了統治。他們在小亞細亞西部最後一個勁敵為艾丁酋長國,後者阻擋了他們獲得西南出海口的通路。 ,奧爾汗獲得了藉口進一步入侵歐洲。1356年其子蘇萊曼帕夏率領大軍橫渡達達尼爾海峽,攻佔了喬爾盧(Chorlu)及狄迪蒙特喬(Didymoteicho),從而打開了通往阿德里安堡(今土耳其埃爾迪內)的門戶。奧爾汗不僅攻城掠地,還將大量土庫曼遊牧民移民至新征服的土地上,使色雷斯開始突厥化。當奧爾汗大約於1362年去世時,土耳其人儼然已成為整個西色雷斯的主宰。奧斯曼人在亞洲也頗有收穫,不過其新領土多數是通過和平手段得到的。薩拉克汗與卡拉西兩個酋長國被吞併了,趁著格米延勢力的衰退,奧斯曼人還成功地在埃斯基謝希爾與安卡拉建立了統治。他們在小亞細亞西部最後一個勁敵為艾丁酋長國,後者阻擋了他們獲得西南出海口的通路。
奧爾汗不僅是一位偉大的征服者,也是一位偉大的統治者。在其兄弟的協助下,他將自己的國家治理得井井有條,並且保持了地方加齊的活力。他通過組建、管理阿克希(Akhis,即藝術家、學者、商人所屬的行會)促進了城市的發展,通過拉攏、爭取阿訇階層穩定了宗教事務。奧斯曼的基督教臣民也得到了相對公平的處置:如果某個基督教城鎮負隅頑抗,城破之後市民將失去權利,其中的五分之一將變為穆斯林的奴隸,很多被送往亞洲做苦工,子女則被送進軍隊(如新軍的成員大多為基督徒青少年)。如果基督徒主動歸降,就能保留自己的信仰與生活習慣。甚至很多基督徒認為奧斯曼人的統治好過拜占庭皇帝,因為前者的稅率要溫和許多。雖然不少基督徒皈依了伊斯蘭教以期獲得政治權利,但是並沒有官方強制要求改宗的政策。而阿訇們每到一地,便開設宗教學校,為蘇丹培養了大量忠心耿耿的精英。
與此同時,軍隊也得到了重組。過去,奧斯曼的軍隊幾乎完全由遊牧民的輕騎兵組成,現在它被設計為兩個部分。一部分士兵獲得一小塊土地,平時耕種,繳納賦稅,而戰時則承擔軍事義務。這塊封地被稱作“蒂瑪”(timar)。更大一些的封地被稱作“紮米特”(ziamet),其領主要負擔更高的稅率,戰時要提供更好的裝備與士兵。最大的一些領主被稱作“帕夏”(pasha)或“桑賈克貝伊”(sanjakbey),甚至獲得最高頭銜貝依勒貝伊(beylerbey,意為“貝伊中的貝伊”,譯注),則要相應承擔最高的義務。除了這些自給自足的部隊以外,還有另一支領取薪水的常備軍——土耳其新軍(Janissary),他們終生為蘇丹服務,並構成了蘇丹的禁衛軍團,其成員一般在基督教奴隸或前基督徒中徵集。(一般公認穆拉德一世創建了新軍軍團,不過早在奧爾汗時期便已出現了雛形,譯注。)在這一時期奧斯曼軍隊的主力為西帕希(sipahis,由上述蒂瑪提供),他們擁有自己的土地,自己籌集裝備、口糧,隨時回應蘇丹的徵集。不過他們在戰役中往往也能得到軍餉,並且通常只參加短期戰役。西帕希多為騎兵,相應地,步兵則被稱作皮亞德(piyade)。其中的弓箭手一般稱作阿贊布(Azabs),他們與巴希巴祖克(bashi-bazouks)類似,為臨時召集的非正規軍,主要為了劫掠和戰利品而戰。(這一部分非正規步兵往往軍紀敗壞,惡名遠揚,譯注。)此外還有輕騎兵,被稱作阿基比(akibi)。奧爾汗堅持為不同軍種設計了不同的軍服,並建立了完備的軍事動員機制。因此,他能夠在任何時間不引人注意地徵集一支訓練有素的大軍。
穆拉德一世(Murad I)繼承了先父奧爾汗的軍事機器。他的希臘裔母親,土耳其人一般稱作Nilüfer(意為“睡蓮”),為一拜占庭邊區男爵之女。他的兄長蘇萊曼帕夏已經先于父親過世(蘇萊曼深受奧爾汗寵愛,若非英年早逝,很有希望繼承大統,譯注),穆拉德則迅速地除掉了同父異母兄弟易卜拉欣,他的弟弟哈里爾不久後也因病去世,至此穆拉德王位的潛在威脅都被掃除了。在即位的最初幾年,他致力於鎮壓帝國亞洲部分埃米爾的反叛,而拜占庭帝國則乘機收復了一些色雷斯的城鎮(不過色雷斯農村的土庫曼人是無法被驅逐一空的)。不過1365年穆拉德率軍重返歐洲,不費吹灰之力便收復了失去的領土,並佔領了亞得裡亞堡(埃爾迪內),後者成為了帝國新都。控制了阿德里安堡,就是扼住了拜占庭的咽喉。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包圍和孤立,它在亞洲的領土早已淪陷,唯一可行的通路僅剩海洋。
此時歐洲對土耳其人的威脅方如夢初醒。威尼斯與熱那亞,出於對其致殖民地與商路的擔憂,開始商討組成聯軍對抗東方異教徒的可能性,不過他們的嘗試卻勞而無功。約翰五世則前往義大利,試圖喚起西方諸國對土耳其人的警覺,並獲得一批西方雇傭軍——然而帝國此時的財力已不允許他這樣做了。當他于1373年回國時,不得不接受了奧斯曼土耳其的宗主權,並交納年貢和為蘇丹提供士兵,他的兒子曼努埃爾還需前往蘇丹宮廷充當人質——拜占庭實質上已淪為奧斯曼的藩屬。作為奧斯曼的僕人,約翰的表現是稱職的。當他的長子安德羅尼庫斯與蘇丹的兒子塞吉(Sauji)密謀造反時,約翰與穆拉德站在了一起。前者很快被穆拉德的軍隊所鎮壓。而當安德羅尼庫斯於1376年至1379年再次反叛並佔領了首都時,質子曼努埃爾在蘇丹的援助下擊敗了兄長,恢復了約翰五世的統治。不過作為代價,曼努埃爾不得不率領拜占庭軍隊配合土耳其人,攻佔了拜占庭帝國在亞洲的最後一個重要城市阿拉謝希爾(名義上承認拜占庭宗主權的特拉布宗除外)。
雖然此刻歐洲諸國已經對局勢深感憂慮,並試圖策劃新一輪十字軍,但在當時真正致力於與土耳其人作戰的唯有在羅德島的醫院騎士團。不過他們首要的對手是隔海相望的亞丁酋長國,兩者的交戰徒令奧斯曼蘇丹坐收漁人之利。——於是土耳其在色雷斯就幾乎暢通無阻了。大批土耳其遊牧民拖家攜口湧向這塊土地。奧斯曼擴張的野心已經難以遏制。塞爾維亞雖然還是巴爾幹半島的重要力量,不過在1355年杜尚國王去世後,已經一分為二。保加利亞此時仍然未從1330年被塞爾維亞人擊敗的災難中恢復過來,但是塞爾維亞的所作所為一定程度上也使自己失去了利用保加利亞充當緩衝國的機會。保加利亞人明哲保身,甚少參與針對土耳其的戰事,唯一例外是1371年他們為南塞爾維亞國王武卡欣(Vukashin)的軍隊派出了一支偏師,然而由於國王指揮的拙劣,聯軍在馬瑞特薩河畔遭到慘敗(土耳其人從兵力上而言是遠處於劣勢的)。這場戰役的勝利也使得穆拉德控制了保加利亞的大部與塞爾維亞、馬其頓。保加利亞國王約翰(John Shishman)不得不承認蘇丹的宗主權,並將自己的女兒塔瑪爾送往蘇丹後宮。而此時統一的塞爾維亞的王公拉紮爾(Lazar)也不得不接受自己的國家淪為奧斯曼土耳其的藩屬的事實。
穆拉德的餘生大部分致力於鞏固他在歐洲的征服。他組織了大量突厥移民進入歐洲,雖然這些殖民活動不如在小亞細亞甚至色雷斯來得順利,但是很快,土耳其的蒂瑪便密佈於希臘、斯拉夫、瓦拉幾亞等地,而貝伊、帕夏們掌控了廣大鄉村。到1386年,穆拉德的領土已西至阿爾巴尼亞附近的莫納斯特爾,北至尼什(今塞爾維亞第三大城市,譯注)。1387年,歷經四年圍攻後,蘇丹拿下了希臘名城塞薩洛尼基。穆拉德對該城頗為寬宏,除任命總督外並未干涉當地民眾的生活。
1381年穆拉德一世在降服了格米延酋長國(Germiyan)後,便開始計畫遠征卡拉曼。他命令歐洲各僕從國家派出軍隊助戰。高傲的塞爾維亞國王拉紮爾視之為奇恥大辱,中斷了對蘇丹稱臣納貢。一支土耳其大軍迅速出動,奪取了尼什,迫使塞爾維亞人再次臣服。不過拉紮爾表面上雖表示恭順,暗地卻組織巴爾幹各國成立聯軍反抗土耳其。1387年在托普利特薩(Toplitsa)河畔,塞爾維亞軍隊取得了對奧斯曼土耳其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大勝。蘇丹迅速做出了反擊。通過向保加利亞急行軍,他降服了當地兩位主要的王公,隨即進入南塞爾維亞,獲取了科斯坦丁王公康斯坦丁的支持,接著他繼續北進,與拉紮爾的主力在科索沃平原(亦稱“黑鳥平原”)相遇。(即科索沃戰役,譯注。)
1389年6月15日清晨,一名塞爾維亞逃兵聲稱擁有重要情報,獲得了面見蘇丹的機會。在蘇丹的帳篷中,他乘其不備,用一把帶毒的匕首刺中了穆拉德心臟(這名勇敢的刺客叫Miloš Obilić,被塞爾維亞人奉為民族英雄,譯注)。蘇丹當即身亡,而他也迅速地被衛兵殺死。這次暗殺頗有傳奇色彩,不過卻是徒勞無功的。蘇丹的王子正在營中。長子巴耶濟德(Bayezit,綽號“雷霆”)迅速掌握了大局,他隱瞞了蘇丹的死訊,全力進行戰役(一說在穆拉德被刺前勝負便已經見分曉了,譯注)。土耳其軍隊訓練有素,紀律嚴明,而相形之下,塞爾維亞聯軍更像一群烏合之眾,一旦戰況不利,便有四分五裂之虞。黃昏時分,土耳其人終於取得了決定性勝利[9]。拉紮爾國王被土耳其俘虜,作為報復,他在穆拉德遇刺的帳篷前被殘忍地處決。此刻巴耶濟德方宣佈自己繼任蘇丹,他果斷地派人勒死了自己的兄弟雅各(Yakub),從而保證了王權的統一(當然這也形成了惡劣的先例,此後蘇丹即位時往往對自己的兄弟痛下毒手,譯注)
穆拉德一世在其30年的統治當中,利用先父遺留下的政權與軍隊,將一個加齊酋長國變為了東南歐首屈一指的強權。他本人儼然便是這個新生國度的象徵。穆拉德與父親、祖父不同,他崇尚壯麗奢華與莊嚴禮儀,他將自己視作皇帝而非酋長。(穆拉德在位時期,不再稱加齊,而是稱蘇丹,譯注。)他性格嚴厲,甚至嚴酷,外加一點玩世不恭(或許這來自他的希臘祖先——穆拉德母親具有希臘血統)。但另一方面,他為人慷慨、公正,極度推崇紀律。
他的繼承人巴耶濟德,也是具有希臘血統,不過據說他母親並非顯貴之女,而是個基督教奴隸,名叫Gulchichek(相當於“玫瑰花”之意)。他繼承了父親對華麗之風的愛慕,但其性格火爆,有些自我放縱,對他人不夠寬容,對紀律要求也不那麼嚴格。雖然因其行事如風一般迅速而得到了綽號“雷霆”(Yilderm),但他並算不上傑出的指揮官。他的統治繼承了父親開創的大好局面。科索沃戰役的勝利使他當之無愧地成為了整個巴爾幹的主宰。看上去假以時日,巴耶濟德必將征服剩餘希臘、阿爾巴尼亞人的領土,統治整個半島。拉紮爾之子斯蒂芬(Stephen)繼承了賽爾維亞王位,但作為土耳其藩屬,他已不再稱國王而是稱“專制君主”(despot),並且,將自己的妹妹瑪利亞(Maria)嫁給了蘇丹。保加利亞王國在1393年被奧斯曼土耳其滅亡,一年後,蘇丹的軍隊征服了伯羅奔尼薩斯。1396年,巴耶濟德進一步計畫征服君士坦丁堡,不過當他抵達城外時,驚聞已有一支十字軍起來反抗他。這支聯軍受教皇號召,由匈牙利國王西吉斯蒙德率領,包含匈牙利、英格蘭、法蘭西、蘇格蘭、波蘭、波希米亞、奧地利、義大利等多國士兵。正如其綽號“雷霆”,巴耶濟德一世迅速回師,並在尼科堡(Nicopolis)決定性地擊敗了十字軍。西方人的愚蠢相當程度上幫助蘇丹獲得了勝利(軍中多國士兵並不聽從西吉斯蒙德號令,尤其是法蘭西騎士不聽指揮擅自發動衝鋒,最終導致了潰敗,譯注)。這次大勝使蘇丹吞併了保加利亞王國的殘餘部分,並使多瑙河畔的瓦拉幾亞公國向他稱臣。在多瑙河前線樹立了權威後,他回到君士坦丁堡城外,不過並沒有立即再度發起圍攻。這部分是因為他聽到傳言:有一支強大的義大利艦隊準備前來援助拜占庭首都。於是,他開始嘗試挑唆拜占庭共治皇帝約翰七世反對其叔叔曼努埃爾二世,他的嘗試失敗了,與拜占庭內亂的傳統相較,約翰七世少見地與曼努埃爾交情甚篤。西方的援軍確實到了,不過僅僅是布錫考特手下的一支偏師而已(Marshal Boucicault,1366-1421,法國元帥,譯注)。他們守衛君士坦丁堡達一年之久,然而在戰場上並無建樹。
目睹西方的所謂支援如此孱弱,巴耶濟德立即開始著手策劃下一次對君士坦丁堡的圍攻。他在拜占庭首都海峽對岸的亞洲修建了阿那多盧要塞(Anadolu Hisar,意為小亞細亞堡),並以此作為軍事基地。1402年,巴耶濟德向拜占庭發出最後通牒,要求皇帝開城投降。此時,曼努埃爾二世正在西方乞援,留守的約翰七世勇敢地對使者回應道:“告訴你家主人,我軍固然孱弱,然而篤信真神,上帝會給予我們克敵力量。蘇丹欲戰欲和,悉聽尊便。”
約翰對上帝的虔誠,隨著東方傳來的消息,變得更加牢固了。帖木爾(Timur)1336年出生於西察合台汗國渴石(Kesh)一個信奉伊斯蘭教的突厥貴族家庭,不過他亦含有成吉思汗女系後裔血統(帖木兒是否帶有蒙古王族血統尚存爭議,但他至少曾迎娶察合台汗國公主為妻,故也被人稱作“駙馬帖木兒”,譯注)。至14世紀末,他已經建立了一個東與中國接壤,南抵孟加拉灣,西至地中海的龐大帝國。無論談及攻城掠地還是冷酷無情,他都堪與自己的祖先成吉思汗媲美。不過他相對缺乏令自己的土地長治久安的才能——一旦他去世,帝國便迅速分裂崩潰了。然而當他在世時,帖木兒依然是一個可怕、兇狠的對手。雖然他是一名虔誠的穆斯林,但他並不算一個傳統的加齊勇士。因為他並非為了信仰而戰,而是為了自己國家的強盛——他偉大的勝利多半來自與穆斯林的征戰。帖木兒一向對奧斯曼土耳其懷有仇恨,部分是因為突厥人之間的嫉妒,部分是擔心奧斯曼的強大會威脅到他的西方行省。早在1386年他就已經入侵安納托利亞東部,並擊敗了爾金迦(Erzinjan)埃米爾的軍隊。隨後他班師回國,不過威脅說隨時還會回來。8年後巴耶濟德通過聯姻獲得了格米延酋長國大片土地,他也親自來到爾金迦視察其帝國東部防線。一年後,帖木兒再次出現在小亞細亞東部,攻陷了錫瓦斯(Sivas)並大肆燒殺,死難者中就包括巴耶濟德的一個兒子,他是作為總督被派來治理該地的。對巴耶濟德而言幸運的是,隨後韃靼人並未繼續西進,而是揮師向東,一路劫掠了阿勒頗、大馬士革與巴格達。然而,蘇丹的麻煩並未結束。當巴耶濟德率領帝國主力包圍君士坦丁堡時,帖木兒向他派來了一名特使,嚴詞要求蘇丹停止軍事行動並歸還以往竊取的拜占庭領土——蘇丹的回應是狠狠地侮辱了來使。隨後巴耶濟德中止了圍攻,帶領部隊回到安納托利亞,而此時帖木兒的兵鋒已再次抵達錫瓦斯。
最後的決戰於1402年6月25日在安卡拉爆發。巴耶濟德的傲慢自負使他的軍隊處於不利境地,加之他的部隊魚龍混雜,很多士兵未經過良好訓練並對蘇丹的吝嗇頗有微詞——當帖木兒的大軍(其中還包括來自印度的戰象)發動猛攻時,奧斯曼的軍隊崩潰了。蘇丹與其第二子穆薩均被帖木兒俘虜。唯一屹立不倒的蘇丹軍團反倒是塞爾維亞君主斯蒂芬的部隊,他成功地救出了巴耶濟德的長子蘇萊曼以及他的一名兄弟。而蘇丹第四子穆斯塔法在戰役中失蹤。帖木兒乘勝進入安納托利亞西部,攻城掠地(其中就包括土耳其前首都布爾薩,當地蘇丹的後宮也被帖木兒盡收囊中),而土耳其殘存部隊則不得不龜縮于阿那多盧要塞以避其鋒芒。一路上巴耶濟德被關押在一台轎子中與帖木兒同行,後來民間以訛傳訛,聲稱巴耶濟德一直被囚禁在一隻黃金牢籠中——事實上,土耳其蘇丹受到了帖木兒的禮遇,他的死因很可能為自盡(1403年3月)。隨後帖木兒釋放了穆薩,並允許他將父親屍體送回布爾薩的皇室墓地。1403年晚些時候,帖木兒離開了安納托利亞,返回其帝國首都撒馬爾罕。他于1405年病逝于遠征中國途中,享年69歲。
此時此刻,如果歐洲諸國盡釋前嫌,一致對外,或許可一勞永逸地根除土耳其之患。不過,雖然土耳其王朝覆滅了(安卡拉戰役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解體,陷入了長時間的“大空位時期”,譯注。),但土耳其問題依然存在。歷史學家固然可以指責西方基督徒失去了打擊土耳其的天賜良機,不過,他們忽略了下述事實:土耳其人早已移民巴爾幹多年,根深蒂固,要壓制其勢力已殊為不易,更遑論將其連根拔起了。雪上加霜的是,帖木兒的勝利反而迫使大量土耳其人,甚至整支部落,前往歐洲避難——熱那亞人通過艦隻將土耳其人送過海峽,並借此大賺了一筆。至1410年,根據歷史學家杜卡斯(Ducas)的記載,在歐洲的土耳其人,其人數已經超過了小亞細亞。何況巴耶濟德還留下了一支不容小覷的軍事力量,足以守衛歐洲前線。誠然,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在安卡拉顏面掃地,其軍力大為削弱,但畢竟沒有到徹底覆滅的程度。
曼努埃爾二世盡可能地抓住這一時機,通過外交手腕來保衛帝國。巴耶濟德的幾名兒子開始了一場王位爭奪戰。長子蘇萊曼在歐洲自立為蘇丹(定都阿德里安堡),不過其地位並不穩固。為了爭取拜占庭帝國的支持,他將塞薩洛尼基及數個色雷斯城鎮歸還於曼努埃爾二世,甚至許諾一旦平息內戰,便將土耳其在小亞細亞的數個城鎮也一併歸還(蘇萊曼還取消了拜占庭帝國的上供的年金,事實上給予了拜占庭平等地位,譯注)。他將自己的幼弟凱西姆送往君士坦丁堡為人質,作為回報,他迎娶了曼努埃爾的侄女(也是摩裡亞專制君主國國王賽奧多爾一世之私生女)。1405年,他擊敗並殺死了自己的兄弟伊薩(Isa)。然而蘇萊曼是一個神經質的統治者,且終日酗酒,常常神志恍惚,他的部下對其喪失了信心,紛紛轉投巴耶濟德另一名兒子穆薩門下(穆薩本與蘇丹一道被俘,獲得自由後投靠其兄弟穆罕穆德,被後者派往歐洲與蘇萊曼作戰,譯注)。1409年,由於眾叛親離,蘇萊曼被穆薩徹底擊敗,並在逃往君士坦丁堡途中被殺。穆薩於是自立為蘇丹,並殘酷地報復了當初支持蘇萊曼的塞爾維亞人。他再次攻陷了塞薩洛尼基,俘虜了為基督徒守城的蘇萊曼之子奧爾汗,並刺瞎其雙目。雖然海戰受挫,但他依然召集了一支陸軍,開始圍困拜占庭首都(1411-1412)。不過此時穆罕穆德已經平定了土耳其位於安納托利亞的領土,開始向穆薩的勢力範圍進軍。在拜占庭、塞爾維亞乃至若干對穆薩殘暴不滿的加齊的共同支持下,1413年,穆罕穆德打敗並殺死了穆薩,成為了新一任蘇丹。
穆罕默德•切萊比,綽號“紳士”,向世人證明了他不僅擅長打天下,同樣善於治天下。他將穆薩奪取的塞薩洛尼基與其他城鎮歸還了曼努埃爾,並在一生中都維持了與拜占庭的良好關係。1416年與1419年,他被迫捲入了兩場與威尼斯、匈牙利的非決定性戰事,同時還鎮壓了所謂從安卡拉戰役中倖存的兄弟穆斯塔法(其身份存疑,亦稱“假穆斯塔法”,譯注)掀起的叛亂。不過他畢生主要的興趣還是在帝國邊境修築要塞,鞏固國內統治與美化城市。留存至今的布爾薩“綠清真寺”(也稱作Yeşil清真寺,譯注)可算他仁慈統治的見證。穆罕默德於1421年11月因中風逝世。
穆罕默德的長子穆拉德(後為穆拉德二世)此時正擔任帝國安納托利亞總督,得知父親死訊後,秘不發喪,星夜趕回了阿德里安堡,順利接管了帝國權力。與他父親一樣,穆拉德本質上也是名和平主義者。據說他深受蘇菲派托缽僧(dervish)影響,甚至嚮往著早日隱退以便過上隱修生活。不過穆拉德亦是一名勵精圖治的君主,時事逼迫他成為了一名優秀的戰士與管理者。此刻覬覦王位者穆斯塔法依然勢大,穆拉德懷疑他暗中得到了拜占庭支援,於是派遣使者前往君士坦丁堡要求曼努埃爾做出澄清,並強調他願意延續自其父輩以來形成的土耳其-拜占庭同盟。曼努埃爾原本傾向於同意,不過此時他已經老邁,政權主要操持在其子約翰八世手中,後者與元老院均認為保持土耳其內亂于己有利。於是約翰八世將假穆斯塔法送回加里波利並引發了新一輪叛亂,作為報復,穆拉德二世在1422年重新發動了對君士坦丁堡的圍攻。然而,此時的君士坦丁堡城牆對缺乏重型攻城設備的土耳其人來說,依然是難以逾越的。約翰八世對政局的預測也不乏合理之處——叛亂果然在安納托利亞爆發了,叛軍名義上處於穆拉德弟弟穆斯塔法的領導之下,然而幕後的指揮者實為格米延與卡拉曼的埃米爾。穆拉德不得不放棄了圍攻,代之以縱軍蹂躪整個伯羅奔尼薩斯。(最終穆拉德在1423年平定了弟弟穆斯塔法的叛亂,而假穆斯塔法也在此之前被擊敗,於逃往瓦拉幾亞途中被殺,譯注。)
雖然穆拉德也渴望和平,然而時局常常令他難以如願。1428年,他率軍擊退了一支越過多瑙河的匈牙利、波蘭聯軍。1430年他入侵了伊庇魯斯的約阿尼納(塞爾維亞人稱Janina)。同年他從威尼斯人手中奪取了塞薩洛尼基,後者一度掌握該城7年之久。塞爾維亞君主斯蒂芬的繼承人喬治•布蘭科維奇(George Brankovich)於1427年上臺後,便一再向蘇丹表達作為封臣的忠心,而蘇丹則要求他退出了與匈牙利的聯盟。隨即穆拉德命令喬治將女兒瑪拉(Mara)送往自己後宮,塞爾維亞人表現出的遲疑令憤怒的蘇丹派出了部隊征討——塞爾維亞已經不再被奧斯曼人信任了。1440年穆拉德的軍隊摧毀了塞爾維亞人在多瑙河畔的要塞斯梅代雷沃(Smederevo),後者本是在蘇丹的允許下興建的。旋即蘇丹的軍隊圍困了貝爾格勒,不過塞爾維亞首都的城防過於堅固,以至於土耳其人不得不無功而返。
貝爾格勒的解圍鼓舞了蘇丹的敵人。猶金教皇在費拉拉-佛羅倫斯大公會議後組建了新一支十字軍。匈牙利國王拉迪斯拉斯(Ladislas)對此十分熱衷,而塞爾維亞君主也表示願意施加援手。阿爾巴尼亞領袖喬治•卡斯翠奧塔(George Castriota),綽號“斯坎德培”,也旋即對蘇丹宣戰;亞洲的卡拉曼埃米爾則被說服同時發起攻擊。當穆拉德忙於平定卡拉曼的叛亂時,匈牙利軍隊及其盟軍,在特蘭西瓦尼亞總督匈雅提的率領下,越過多瑙河,將土耳其人逐出了塞爾維亞。穆拉德急忙回師歐洲,向多瑙河進軍。但他並不願冒險輕啟戰端,而匈牙利國王拉迪斯拉斯對此也心有戚戚。此刻匈牙利部隊得到了教皇從西方召集的援軍的支持(由教皇特使朱利安主教指揮),但拉迪斯拉斯對這些援軍並不滿足。1444年6月,他與穆拉德在塞格德(Szeged,今匈牙利第三大城市,譯注)舉行會晤,隨後,蘇丹以古蘭經,國王以福音書互相起誓,允諾實現為期十年的停戰協定,期間他們以多瑙河為邊界。匈雅提對停戰協定並不認同,故未參與其中。
穆拉德以為,終於可卸下重擔,開始他嚮往已久的隱修生活了。然而,正當他撤回部隊並表達出退位意願之時,前方傳來了匈牙利軍隊越過多瑙河,進抵保加利亞的消息。教皇特使朱利安主教認為,與異教徒所定的盟約是不需要遵守的,而眼下正是擊潰土耳其人的天賜良機。如此明目張膽的背信棄義令東正教徒與土耳其人均感到震驚。拜占庭皇帝約翰八世明確表示拒絕為匈牙利人提供幫助。喬治•布蘭科維奇也撤回了本國軍隊並阻止斯坎德培提供援助。匈雅提不情願地加入了部隊,但教皇特使對他關於戰略的真知灼見置若罔聞。穆拉德此刻本已回到安納托利亞安排隱退事宜,得知情況有變,立即回師討伐。1444年11月11日,穆拉德在瓦爾納擊敗了兵力三倍於他的基督教聯軍。拉迪斯拉斯與朱利安主教雙雙陣亡,唯有匈雅提及其部隊全身而退。這場勝利奠定了蘇丹對多瑙河流域的控制權。
不久之後,穆拉德將王位正式傳予年僅12歲的兒子穆罕穆德,退休至馬尼薩。然而或許命中註定,穆拉德二世必將無緣清閒,他的大臣與軍隊對新任蘇丹產生了不滿。穆罕穆德被認為早熟、固執且傲慢無禮,而此時偏偏歐洲前線又出現了難題——斯坎德培[11]在阿爾巴尼亞一再挫敗土耳其的進犯。公眾的呼聲與政治形勢迫使穆拉德不得不再度出山(穆罕穆德二世於1444-1446年統治兩年後,穆拉德恢復了蘇丹身份,一直統治到1451年去世為止,穆罕穆德二世於1451年再次繼任蘇丹,譯注)。1446年,穆拉德再次派遣軍隊蹂躪了伯羅奔尼薩斯半島。1448年,匈牙利攝政匈雅提•亞諾什率領一支由匈牙利、瓦拉幾亞、波希米亞、日爾曼人組成的軍隊恢復了對土耳其的攻勢,他甚至與斯坎德培約定會師于科索沃平原。然而在阿爾巴尼亞人到來之前,一支土耳其大軍旋風般地出現,並摧毀了他的軍隊。在波希米亞與日爾曼軍隊的拼死護衛下,匈雅提勉強逃離了戰場。與瓦爾納的失利接踵而至的這場慘敗,導致了匈牙利在整整一代人的時間裡軍力不振。雖然匈牙利的軍旗依然在貝爾格勒飄揚,但是它再也無力跨過多瑙河對土耳其採取行動了。當君士坦丁堡的危機爆發時,匈雅提•亞諾什愛莫能助,無計可施。在整個巴爾幹,此時唯有阿爾巴尼亞山區的斯坎德培尚能與土耳其一較短長。
穆拉德二世在安納托利亞同樣取得了成功。之後的幾年裡,蘇丹吞併了艾丁與格米延酋長國,並成功地震懾了卡拉曼。其他自治的王公(例如錫諾普)也紛紛承認奧斯曼的宗主權。而特拉布宗皇帝與他在君士坦丁堡的連襟一樣虛弱,不得不表示對蘇丹的恭順。此時的奧斯曼帝國,繁榮昌盛,秩序井然。帝國軍隊的核心為土耳其新軍(The Janissaries)。穆拉德完善了德米舍梅制度[12](即所謂“血供”),從而定期地從帝國基督教臣民中招募男孩,經過嚴格的伊斯蘭化訓練,部分特別優秀的可以進入宮廷或充當技師,不過大部分都成為了未來的新軍戰士。作為蘇丹的禁衛部隊,新軍擁有自己獨立的軍營,並被禁止結婚,從而終生為蘇丹效力。儘管有這種令人反感的“血供”制度,儘管偶爾也存在強制基督徒改宗的情況,穆拉德在帝國的基督教臣民中還是受到了歡迎,因為他們發現這位統治者大體上還是公正與謹慎的。蘇丹有很多基督教摯友,據說還尤其受到他美麗的塞爾維亞妻子的影響。確實,在他的有序與寬容的統治下,很多希臘裔臣民發現其生活要遠比處於基督教國家統治下輕鬆、幸福。
穆拉德二世於1451年1月13日在阿德里安堡逝世,為他的繼任者留下了一筆豐厚的遺產。那一年,穆罕穆德蘇丹19歲。
注釋:
[1] 放任亞美尼亞被塞爾柱人攻佔是拜占庭的重大失誤。從此,安納托利亞東部的防務就開始解體了。亞美尼亞人,埃德薩的馬修(Matthew of Edessa)曾寫道:“這個國家是由無恥荒淫的‘希臘’人,親手送給土耳其人的,他們毀滅我們自己的王室,解散了我們勇敢的貴族,並取消了我們一切可供自衛的工具。”參見: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一》,345頁。
[2] 這是一個蘇菲派術語,大致意思相當於通常所說的“美德”,對加齊而言,更類似與西方人所謂的“俠義精神”、“騎士精神”。這一理念於10-11世紀開始形成,並在穆斯林世界的各個行會、社團中廣泛流行。譯注。
[3] 阿萊克修斯統治時期曾向教皇烏爾班二世(Urbanus II)求援,後者於1096年召集了第一次十字軍,對帝國收復小亞細亞西部也起到了重要的援助作用,阿萊克修斯的女兒安娜•科穆寧娜為拜占庭著名歷史學家,著有《阿萊克修斯傳》,為此段歷史留下了寶貴資料,譯注。
[4] 1204年,原本計畫出發征討穆斯林的十字軍在威尼斯人慫恿下,借助拜占庭內亂之機,攻陷了君士坦丁堡,並建立了拉丁帝國。拜占庭帝國四分五裂,大傷元氣,至1261年方由尼西亞流亡政府收復首都。十字軍多信奉天主教,其背信棄義的行為在東正教徒心中留下了長久的傷痕,2001年羅馬教皇保羅二世訪問希臘時,希臘大主教克裡斯托杜洛還在要求教宗為1204年洗劫君士坦丁堡一事鄭重道歉。譯注。
[5] 此處存疑,斯坦福肖《奧斯曼帝國》一書記載埃爾托格魯爾去世於1280年左右,而黃維民《中東國家通史•土耳其卷》則認為他死於1288年。參見:斯坦福•肖:《奧斯曼帝國》,許序雅、張忠祥譯,西寧:青海出版社,2006,第21頁。黃維民:《中東國家通史•土耳其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49頁。譯注。
[6] 比較傳統的觀點認為,奧斯曼王朝的祖先為一名叫做蘇萊曼•沙赫的土庫曼部落首領,他在13世紀初,為了躲避蒙古人的入侵而來到中東,不過在橫渡幼發拉底河至敘利亞的中途,他不幸溺水而亡,其部眾隨即分裂。大部分回到了呼羅珊,為蒙古人服務;而他的一個兒子,即埃爾托格魯爾,率領家族剩餘成員來到了安納托利亞。為了生存,他開始成為羅姆蘇丹國的附庸,以協助蘇丹對抗拜占庭人與蒙古人。據說,作為回報,蘇丹將安納托利亞西部以及弗裡吉亞(Phryga)的幾塊土地贈與埃爾托格魯爾,這也是日後奧斯曼帝國的初始。但通過近來發現的13世紀史料可以推知,奧斯曼人的祖先似乎不是在13世紀為躲避蒙古人而來,相反,早在11世紀曼奇克特會戰後,便已經湧入小亞細亞。在將近兩個世紀的時間裡,奧斯曼的先人僅僅是普通牧民或傭兵。奧斯曼人後來宣稱的顯赫祖先,很可能是為了強調自己統治的正當性。參見:斯坦福•肖:《奧斯曼帝國》,20-21頁。譯注。
[7] 此處所說奧林匹亞山(Mount Olympus)並非通常意義上希臘眾神的居所及現希臘最高峰(海拔2917米),而是在今土耳其布爾薩省(安納托利亞西北)境內,為加以區分,歷史上稱作密西亞的奧林匹亞山(Mysian Olympus),海拔2543米。其現代土耳其名為烏盧達山(Uludağ)。譯注。
 內戰初始階段的勝利使坎塔庫震努斯成功獲得了共治皇帝身份,時稱約翰六世,不過他過分依賴奧斯曼雇傭軍並使土耳其人進入歐洲的行為激起了民眾不滿,最終被迫下野。坎塔庫震努斯是拜占庭末期有為的政治家,平心而論,其才華強於年輕的約翰五世,如果他在內戰中最終取勝,或許拜占庭的國運還可多延續一段時間。譯注。 內戰初始階段的勝利使坎塔庫震努斯成功獲得了共治皇帝身份,時稱約翰六世,不過他過分依賴奧斯曼雇傭軍並使土耳其人進入歐洲的行為激起了民眾不滿,最終被迫下野。坎塔庫震努斯是拜占庭末期有為的政治家,平心而論,其才華強於年輕的約翰五世,如果他在內戰中最終取勝,或許拜占庭的國運還可多延續一段時間。譯注。
[9] 基督徒軍隊由塞爾維亞及波士尼亞人組成,拜占庭皇帝並未參加此次戰役。科索沃戰役的失敗摧毀了巴爾幹及多瑙河南岸塞爾維亞最後一次有組織的抵抗,此後歐洲東南部僅剩匈牙利是蘇丹需要提防的對手了。直至今日,塞爾維亞人還在紀念這場戰役。對於這次戰役的人數規模,不同史料記載出入較大。如斯坦福肖在《奧斯曼帝國》一書中認為基督教聯軍超過了10萬人,而土耳其聯軍人數在6萬左右。而約翰•考克斯於他的《塞爾維亞史》一書中,稱科索沃戰役時,土耳其方面兵力為30000至40000,基督教聯軍兵力僅有15000-25000。參見:斯坦福•肖:《奧斯曼帝國》,第32頁。John K. Cox, The History of Serbia, Greenwood Press, 2002, p.30.譯注。
[10] 斯蒂文先生原文中認為帖木兒享年72歲,似有誤。帖木兒生於1336年,去世於1405年,故應為享年69歲。參見:克拉維約:《克拉維約東史記》,楊兆鈞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153-155頁。大英百科全書線上版“帖木兒”詞條:http://www.britannica.com/EBchecked/topic/596358/Timur
[11] 喬治•卡斯翠奧蒂(1405-1468年),拜占庭貴族後裔,曾作為人質為奧斯曼宮廷效力,並被迫皈依伊斯蘭教,取得戰功後,獲得“亞歷山大貝伊”(İskender Bey)稱號,在阿爾巴尼亞語中稱Skënderbe shqiptari,這便是他的綽號“斯坎德培”的由來。1443年,斯坎德培公開反抗土耳其統治,改宗天主教,成為阿爾巴尼亞民族英雄。他一生堅持抵抗土耳其人,作戰25次,獲勝24場,成為蘇丹在巴爾幹的勁敵。但在他去世後,阿爾巴尼亞戰局日漸不利,最終於1501年被奧斯曼帝國徹底征服。譯注。
[12] 德米舍梅(Devşirme)一詞原指統治者有權佔有五分之一戰利品的徵收程式。後來,它發展為奧斯曼土耳其官方對基督徒家庭兒童定期招募的制度,以充實帝國軍隊、宮廷或政府職位。新軍士兵(包括整個奧斯曼中央常備軍“卡皮庫魯”)一般也通過德米舍梅制度入伍。德米舍梅最早成型約始于巴耶濟德一世時期,普遍實施則是在穆拉德二世及穆罕穆德二世時期。該系統在其運行初期或許遭到了部分基督徒的抵制,甚或被作為蘇丹迫害他們的證據,不過隨著時間推移,基督徒們發現這是令自己子孫進入帝國高層的絕佳方式,於是被蘇丹徵集漸漸演變成了一種基督徒的福利和榮譽,甚至有部分基督徒家長採用賄賂的方式,以安排兒子被蘇丹選中。參見:斯坦福•肖:《奧斯曼帝國》,第151-152頁。黃維民:《奧斯曼帝國》,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172-177頁。譯注
|
| Nineveh |
Posted - 11/25/2011 : 15:09:35
第一章 垂死的帝國
1400年耶誕節,英王亨利四世在他位於伊森(Eltham)的行宮舉行了一次宴會,不僅為了慶祝佳節,更重要的是為了歡迎他的一位特殊貴客——希臘人的皇帝(有時候也被稱作羅馬人的皇帝)曼努埃爾二世(Manuel II Palaiologos)。後者已經遊歷了義大利,並曾於巴黎短暫駐留。期間法王查理六世一度將盧浮宮妝點一新,以款待這遠道的貴賓。
英國人為拜占庭人的高貴舉止所傾倒,他們潔白如玉的長袍也令人們印象深刻。然而,儘管皇帝身份高貴,頗得好感,英法兩國王公貴族們卻只能令其敗興而歸——皇帝此行專為祈求西方基督教國家援助,以對抗東方入侵的穆斯林異教徒而來,然而他的夢想落空了。亨利國王的大法官亞當(Adam) 回憶道:我細細忖量,如此高貴的基督教貴族卻被東方的薩拉森人逼迫得走投無路,以致要遠赴西方乞援,這是多麼可悲。哦,古羅馬的榮耀如今何在?
確實,古羅馬帝國早已今不如昔。雖然曼努埃爾是奧古斯都及君士坦丁光榮的繼承人,然而,君士坦丁堡的羅馬皇帝可以在羅馬世界呼風喚雨的時代已經逝去。對西歐人而言,他們僅僅是希臘人或拜占庭的君主,已經無法與西歐新興的君主們等量齊觀。直到11世紀拜占庭依然是一股令人敬畏的力量,是基督教世界抵禦穆斯林衝擊的中流砥柱。拜占庭一直成功地扮演了他們的角色,直到11世紀中葉東方的土耳其人興起。於此同時,西方的諾曼人也開始嘗試入侵拜占庭。拜占庭帝國陷入了東西兩線作戰的困境。以帝國義大利領土的失陷為代價,諾曼人終於被擊退了;然而對土耳其人,帝國則永久性地失去了帝國的 糧倉與兵源地——安納托利亞。[1]此後帝國一直面臨兩線作戰之虞,而十字軍運動的興起令局面更加複雜。雖然作為基督徒,拜占庭人對十字軍抱有好感,然而他們長期的政治經驗證明應當對異教徒保持一定寬容並允許其存在。十字軍宣導的聖戰在拜占庭看來反而是危險的和不切實際的。
當然,拜占庭人也希望通過十字軍獲得好處。然而,這一切需要以實力作為基礎。拜占庭繼續以強權面目出現,不過其國力已經開始不斷下降了。在那個充滿戰爭衝突的年代,安納托利亞的喪失,迫使拜占庭皇帝不得不愈發依賴外國盟軍與雇傭軍,而後者是需要以商業特權或金錢作為代價的。這一切不幸又發生在帝國經濟衰退的年代。整個12世紀,帝國看上去似乎依然是富裕和強大的,市場港口商賈如雲,皇帝依然受到尊敬。但是,拜占庭既不支持穆斯林對抗十字軍,也同樣對十字軍缺乏熱情,這就埋下了憂患的種子。同時,11世紀,宗教分歧也加劇了東西方基督教國家的矛盾(1054年,東西方教會互相開除對方教籍,標誌兩大教會公開分裂,譯注)。至12世紀,天主教會與東正教會已經明顯地處於分裂狀態了。
真正的危機是十字軍帶來的。1204年,在軍隊領袖野心的蠱惑下,出於威尼斯人的嫉妒與貪婪,出於天主教會對東正教會的敵意,原本是去援救拜占庭帝國的十字軍反戈一擊,攻佔並洗劫了君士坦丁堡,在其廢墟上建立了拉丁帝國。這一事件終結了東羅馬帝國的強國地位,雖然其並未徹底滅亡。大約半世紀後,流亡至小亞細亞西部的拜占庭勢力(即尼西亞帝國)奪回了君士坦丁堡,擊敗了拉丁帝國。似乎拜占庭帝國又迎來了偉大的復興。然而,米哈伊爾八世的政權(即帕列奧列格王朝,拜占庭末代王朝)已經沒有了昔日的強盛。它還依稀保留了一些過去的威名,君士坦丁堡依然是“新羅馬”,是東正教的中心。拜占庭皇帝,至少在東方人看來,依然是羅馬人的皇帝。實際上,拜占庭已經淪為了一個普通王國,甚至在希臘人世界中亦不是唯一的統治者。在它的東面,有事實上獨立的特拉比宗王國(由拜占庭科穆甯皇室後裔在1204年建立),後者擁有豐富的銀礦和與大不裡士的傳統商路。在色雷斯地區,出現了伊庇魯斯專制君主國(同樣由前拜占庭皇室後裔建立),它一度與尼西亞帝國展開收復君士坦丁堡的激烈競爭,甚至曾經兵戎相見,不過最終也走向衰敗。在巴爾幹,保加利亞與塞爾維亞成為另外兩大勢力。而在希臘本土與周邊島嶼上,義大利人的殖民地與法蘭克人的貴族領地星羅密佈。為了驅逐威尼斯人的勢力(其為十字軍奪取君士坦丁堡的幕後黑手,遭到拜占庭人的普遍厭惡),拜占庭政府引入熱那亞人,後者則要求貿易特權,首都北部的加拉塔(Galata)與佩拉(Pera)商業區隨即為熱那亞人控制,熱那亞商人順理成章地掌握了拜占庭商業命脈,令帝國的財政進一步雪上加霜。而帝國四周可謂險象環生:在義大利有前拉丁帝國的復辟勢力,巴爾幹的斯拉夫王族們則覬覦著皇帝的頭銜。東方的土耳其人一度沉寂了一段時間,這某種程度上也挽救了拜占庭帝國。不過在偉大的酋長奧斯曼的率領下,土耳其人很快再度成為了帝國的勁敵。因為西部的軍事威脅,拜占庭不得不將多數財力人力投入其中,以至於忽略了東部的防禦,這為奧斯曼人在小亞細亞的擴張提供了良機。
14世紀對拜占庭帝國而言是一個災難性的世紀。強大的塞爾維亞王國一度有併吞拜占庭帝國的趨勢。而雇傭軍卡特蘭軍團的叛亂(Catalan Company,即“加泰羅尼亞軍團”)令諸行省一片狼藉。帝國長期陷入內戰之中,各王室成員爭權奪利,內鬥不止。例如約翰五世在其50年的皇帝生涯中,先後三次被廢黜,一次被他的岳父,一次被他的兒子,另一次是他的孫子。禍不單行的還有瘟疫。1347年伴隨內戰爆發的黑死病,奪去了帝國三分之一的人口。奧斯曼土耳其則利用拜占庭與巴爾幹諸國的混亂大肆擴張,至14世紀末,其勢力已經抵達多瑙河畔(Danube),拜占庭已經淪為土耳其領土環繞下的孤島。此時的拜占庭,實際控制地區只限於首都君士坦丁堡,色雷斯的幾座城鎮,黑海沿岸的一些市鎮,幾座小島,塞薩洛尼基(Thessalonica,帝國第二大城市)以及伯羅奔撒半島大部。在這些拜占庭勢力範圍中,還間布著一些拉丁帝國遺留的封建領地,法蘭克人、佛羅倫斯公爵以及威尼斯人都擁有自己的控制區域。其餘的拜占庭原領土則早已被土耳其人奪取。
出人意料的是,雖然此時期拜占庭國力衰弱,然而文化藝術領域卻頗為多產。帕列奧列格王朝也可算一個重視學術與藝術的朝代。例如君士坦丁堡柯拉教堂(Church of Holy Savior in Chora)保存的14世紀初期壁畫與馬賽克鑲嵌畫,就足以令同時期義大利藝術相形見絀。在君士坦丁堡和塞薩洛尼基,還擁有大量同等水準的畫作。當然,藝術創作會受到資金短缺的困擾。帝國的財政已是江河日下,大不如昔了。1347年約翰六世的加冕禮上,其皇冠的寶石居然是用玻璃代替。至14世紀末期,經濟拮据對文化藝術的負面影響開始彰顯。在這期間只有伯羅奔尼薩斯的米斯特拉(Mistra)地區和阿索斯山(即希臘聖山 Mount Athos)附近湧現出新建的教堂,其內部裝飾也較過去節儉。當然學術領域相對較少受到財政因素的干擾。君士坦丁堡大學在13世紀末被帝國賢臣賽奧多爾[3]重建,在他的大力宣導與支持下,14世紀初拜占庭湧現了一大批優秀學者。其中的代表人物,如歷史學家尼基弗魯斯•格雷戈拉斯(Nicephorus Gregoras)、神學家格裡高利•帕拉馬斯(Gregory Palamas)、神秘主義者尼古拉斯•卡巴西拉斯(Nicholas Cabasilas)、哲學家德米圖斯•西多內斯(Demetrius Cydones)與阿金迪納斯(Akyndinus)——都曾在君士坦丁堡大學深造並受賽奧多爾的影響。約翰•坎塔庫震努斯(John Cantacuzenus)[6]被認為是他的繼承者,雖然部分精英對其篡位行為頗有微詞。這一時期的拜占庭知識界,學術氣息濃厚,人才輩出,論爭自由,並且很好地繼承了兩千年以來的希臘學術傳統。他們討論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討論語義學與邏輯學,自然,也會涉及到神學話題。但東正教傳統對哲學往往心存顧慮。雖然優秀的神父一般也願意接受哲學教育,並且運用柏拉圖式的修辭學與亞里斯多德的方法論,但他們的神學是隱晦而非直接的[7]。既然上帝的存在已超出了人類認知範圍,哲學對於解決宗教問題也就顯得力有不逮了。然而,到了14世紀中期,學術界出現了分裂。部分學者受西方羅馬教會的影響,開始攻擊東正教及其神學理念(尤其是其中神秘主義的部分);另一部分學者則極力維護東正教傳統,昔日的朋友成為了論爭中的敵手。“改革派”往往帶有一定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色彩,而“保守派”(代表為帕拉馬斯)則顯得更加因循守舊,後者在僧侶與普通民眾中獲得了大量支持者。(不過“保守派”中也包括諸如約翰•坎塔庫震努斯、尼古拉斯•卡巴西拉斯這樣的人文主義者,因此,“保守派”佔據上風並不能簡單地定性為蒙昧主義的勝利。)
這番論爭不僅是學術問題,也是政治問題。——這關係到是否與西方羅馬教會及天主教國家聯合。而東西方教會長期的分裂及交惡,最終使保守派在這場鬥爭中佔據上風。不過,還是有很多具有遠見的拜占庭政治家看出,脫離西方基督教國家的援助,拜占庭註定無法長期生存。如果西方援助是以東正教會與天主教會共融為前提的,那麼這也是不得不付出的代價。米哈伊爾八世為了對抗西方復辟拉丁帝國的計畫,不惜于里昂大公會議上代表人民同意與羅馬教會共融,但此舉遭到了國內民眾的普遍憎恨。面對民意洶洶,他的兒子安德羅尼庫斯二世不得不推翻了父親的決策。如今,土耳其人已在磨刀霍霍。與西方教會的共融迫在眉睫,這不僅是為了得到西方雇傭軍,更重要的是要聯合基督教國家,共同對抗東方的異教徒,而東正教世界是無力提供強大援助的。多瑙河流域及高加索地區諸王公實力有限且自身不保,俄國人自身問題成堆,鞭長莫及。不過,西方天主教國家真的會援助已經分裂的東方教會嗎?他們是否會把土耳其人的入侵當做對拜占庭的“天譴”而袖手旁觀?帶著這些疑問,約翰五世皇帝于1369年啟程前往教廷進行外交活動,並向教皇表示歸順之意。然而他謹慎地未將其臣民捲入其中,雖然他內心也幻想拜占庭人與他一道走向教會和解之路,然而在當時這是沒有基礎,註定會失敗的。
米哈伊爾八世與約翰五世是政治家,而非神學家。對他們而言,與西方聯合,政治上的裨益高於一切。然而對神學家來說,情況就很棘手了。早在基督教歷史早期,東西方教會在禮拜方式、神學理念等方面就存在分歧。其中最尖銳的矛盾是關於聖靈如何產生以及對“和子說”(拉丁語 Filioque,相當於英語and from the Son)的態度,這也是1054年雙方革除對方教籍的神學原因之一[4]。此外兩大教會還存在許多較小的分歧。西方教會不承認東方教會新近通過的關於“上帝既是實體的,也是精神的”(Essence–Energies distinction)這一教義 。而東正教會同樣對羅馬教會關於“煉獄”的說法不敢苟同。聖餐儀式上所用面餅是否應當發酵成為雙方爭議的又一個焦點。對東方教會而言,西方教會採用無酵餅的做法似乎是師從猶太人,並且罔顧了發酵餅對聖靈的象徵。與之類似,西方教會在聖餐中拒絕使用“求降聖靈文”(Epiclesis)也被認為是大不敬的,東正教會相信,缺乏這一道程式,將令面餅與葡萄酒的神聖性功虧一簣。對於普通信眾如何兼領聖體聖血(Communion under both kinds)及在俗司鐸(Secular priests)能否結婚,兩大教派同樣爭執不休。不過,雙方最大的分歧集中在教會管轄許可權方面。羅馬教宗是否在基督教會中享有居先權或至高地位?按照拜占庭傳統,所有主教一律平等。無人(甚至包括聖彼得之傳人,儘管其見解是受到尊重的)能夠強迫他人接受教義。唯有大公會議(Oecumenical Council)有權對教義進行詮釋。羅馬人對基督教教義的增添(如“和子說”,譯注)令東正教徒大為震驚,不僅因為神學方面的理由,更重要的是,此舉單方面地篡改了由大公會議通過的神聖教義。基於傳統,東正教徒無法接受羅馬的管理與訓誡,它理應由五大宗主教 (Pentarchy of Patriarchs)共同行使,儘管羅馬教宗地位崇高,他也無權僭越其餘主教。拜占庭人篤信其傳統與教規,不過,為了教會的和諧運轉,他們也能在枝節問題上求同存異,這為與西方的和解提供了某種彈性。反倒是羅馬天主教會,基於其天性,輕易不願做出妥協。 (Pentarchy of Patriarchs)共同行使,儘管羅馬教宗地位崇高,他也無權僭越其餘主教。拜占庭人篤信其傳統與教規,不過,為了教會的和諧運轉,他們也能在枝節問題上求同存異,這為與西方的和解提供了某種彈性。反倒是羅馬天主教會,基於其天性,輕易不願做出妥協。
拜占庭的學者們分裂了。相當一部分由於忠於自己的教派而無法認同與羅馬聯合。然而不少學者(尤其是哲學家),願意接受羅馬教廷的權威以使自己的才華得到發揮。基督教國家與基督教文明的和諧統一對他們而言是同等重要的。他們中的一些人曾遊歷義大利,並目睹了當地的活力與生機。他們也發現了,如果作為朋友身份到來的話,他們會受到義大利人何等的敬重。大約在1340年,德米圖斯•西多內斯將湯瑪斯•阿奎納[5](Thomas Aquinas)的著作翻譯為希臘語。阿奎納的學說吸引了大批拜占庭學者,使後者意識到義大利的學術早已非吳下阿蒙。他們渴望與義大利的學術交流,而這一願望也並未落空。越來越多的拜占庭學者在西方獲得了職位與尊敬。融合拜占庭與義大利文化的想法,變得越發具有吸引力。考慮到羅馬歷史上的崇高地位以及當下義大利的繁榮,拜占庭人的某種妥協也未必是難以接受的吧?
然而,“聯合派”的擁躉只限于部分政治家與知識份子,僧侶階層大都表示強烈反對。他們較少受到與義大利學術交流的影響,而是醉心於自己的信仰與傳統。拉丁帝國當年的嚴酷統治給他們留下了刻骨銘心的印記。僧侶們在民眾當中宣傳聯合的種種惡果,甚至聲稱此舉將遭致天譴。任何一位拜占庭皇帝試圖與之對抗都是艱難的,何況還有相當一部分知識份子、神學家贊同僧侶們的觀點,一部分政治人物也對西方的援助心存顧慮。
上述激烈的論爭發生在一個大衰退的年代。儘管擁有優秀的學者,君士坦丁堡已然淪為了一座垂死的城市。12世紀時,首都及近郊人口多達百萬之巨,而今只剩下不足10萬。橫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首都郊區大半也落入土耳其人之手。而金角灣的佩拉大區由熱那亞人所控制。昔日君士坦丁堡附近市鎮、修道院星羅密佈,如今只剩下零落的一些村莊環繞在破敗的教堂四周。拜占庭首都在極盛時期,城內各區分佈著大量花園與公園,而今不僅一些居民區已經消失,花園也被菜地、果園所取代。14世紀中期到訪的著名穆斯林旅行家伊本•巴圖塔(ibn Battuta)計算出城牆內共有13塊小型居民區;西班牙旅行家克拉維約(Gonzalez de Clavijo)也曾對這座宏偉巨城的破敗驚詫不已。佩德羅•塔法(Pero Tafur,西班牙旅行家,1410-1484)於1437年談到君士坦丁堡人口的凋零程度——很多居民區完全是一副鄉村的景象,春天城市裡盛開著大量野玫瑰,入夜後, 夜鶯在樹林裡歡唱。
不僅平民區殘破不堪,甚至連君士坦丁堡東南的舊皇宮也已經無法居住。拉丁帝國末代皇帝鮑爾溫二世在山窮水盡之際,不僅將自己的太子交給威尼斯債主作為“抵押”,更將拜占庭皇宮的屋頂拆除出售以套現。此君亡命天涯後,光復拜占庭的米哈伊爾八世及其繼承者再也沒有財力將皇宮修繕一新。昔日的大競技場(Hippodrome of Constantinople)也僅剩斷壁殘垣,旁邊的“主教宮”(Patriarchal Palace)名義上仍然是教長駐地,不過君士坦丁大牧首也不再“冒險”居住在這搖搖欲墜的殿宇中了。城區多數教堂也已經年久失修,只有偉大的聖索菲亞大教堂(Hagia Sophia)還保留著往日的榮光。
君士坦丁堡的主幹道——梅塞大道(Mese,“中央大街”之意),自查瑞休斯門(Gate of Charisius,今天土耳其人稱為阿德里安堡門)起始,最後抵達舊皇宮。這是首都最繁華的大街,商店住宅鱗次櫛比,途經最重要的建築為全市第二大教堂聖使徒教堂。不過後者也已經殘破不堪了。另一片繁華區位于金角灣沿岸。皇帝的新行宮就位於此處一座小山下。威尼斯也在這一帶港口擁有自己的社區,不僅為威尼斯人提供便利,也聚集了來自安科納、佛羅倫斯、拉古薩甚至加泰羅尼亞的商人,附近甚至還有猶太社區。這裡貨棧碼頭密集,帝國也允許土耳其人在此開設巴紮(市集)。不過以上各區用城牆或柵欄劃分開來,彼此相對獨立。城市每年還要接待遠方的朝聖者,他們多半來自俄羅斯,由此一批旅館應運而生。此外城市也保留了足夠的醫院甚至孤兒院,為市民們提供基本的福利。不過除去這些繁華地帶,君士坦丁堡市區大部分地方已經是空曠和破敗的了。
此時帝國第二大城市為塞薩洛尼基。它仍然是巴爾幹重要的港口,與君士坦丁堡相較,它甚至更加繁榮,其一年一度的集市吸引了各地的大批商人。甚至相對狹小的城市規模也成了它的優勢,這讓它與空空蕩蕩的首都相比,顯得不至於那麼寒酸和破敗。不過該城在14-15世紀同樣命運多舛。它一度被當地起義的平民攻佔並統治了8年之久(革命者被稱作Zealots,反對貴族統治,要求重新分配社會財富,他們於1342-1350控制了塞薩洛尼基。譯注。),在他們被鎮壓前,大批城市宮殿、市場、建築遭到了洗劫與破壞。隨後塞薩洛尼基又遭土耳其人攻佔。雖然希臘人一度將其收復,然而它再也難回到當年的繁榮了。伯羅奔尼薩斯半島值得一提的城市還有摩裡亞(Morea)專制君主國(摩裡亞理論上屬於拜占庭帝國,但一般由拜占庭太子或王子統治,享有自治權。譯注。)首都米斯特拉斯,不過這所謂的“首都”不過是一座宮殿,一座城堡,外加幾座教堂、修道院和學校,比一座村莊規模大不了多少。
1391年,曼努埃爾二世得到了拜占庭帝國這份凋零的遺產。皇帝本人可謂生世多艱:他的青少年時代幾乎都在戰爭與家族內鬥中度過,營救因欠債被威尼斯人扣押的父皇約翰五世也一度成為他的任務。作為皇子,曼努埃爾二世長期在土耳其蘇丹的宮廷充當人質,甚至違心地指揮一支拜占庭軍團為蘇丹攻打希臘人的城市阿拉謝希爾(Alaşehir,綽號“小雅典”,位於小亞細亞,譯注。)。在這段令人心酸的時光裡,學術成為了他最大的安慰。曼努埃爾二世飽讀經書,具有很高的文化素養。他是個有才能的君主,曾經主動將皇位讓與其侄約翰七世,這一慷慨之舉很大程度上彌合了王室內部的紛爭[9]。他曾經盡力修繕帝國的修道院並提高其待遇標準,他給予了君士坦丁堡大學力所能及的最大經費。皇帝清晰地看出西方援助的重要性,並做了大量外交努力。1396年教皇再次召集了一隻十字軍(不過這支軍隊更多是為了援救匈牙利王國而非拜占庭,雖然均是以土耳其為敵),然而因為部隊領導人的荒唐最後在多瑙河畔的尼克波利斯遭到失敗(尼克波利斯的十字軍是歐洲最後一次大規模援助東方的十字軍)。曼努埃爾二世對法國的外交攻勢獲得了一定成果,1399年法王向君士坦丁堡派遣了一隻部隊,不過這支軍隊僅千餘人規模,實在是杯水車薪,於事無補。然而,皇帝反對東西教會的再次共融,一方面是因為自身的宗教信念,一方面也是因為他深知這一方案難以在民間推行。他還告誡自己的兒子,未來的約翰八世,既要與西方友好協商教會聯合事宜,同時又要對內宣稱該聯合絕不會真正實施。當他於1400年左右前往西方國家斡旋時,恰逢天主教會大分裂時期[10](the Great Schism),因此拜占庭皇帝極力淡化其宗教身份而是以世俗統治者的身份尋求援助,以減少宗教紛爭的干擾。但是,雖然皇帝的優雅風度獲得了歐洲貴族的好評,實際的援助卻屈指可數。1402年曼努埃爾二世甚至不得不中斷訪問趕回君士坦丁堡,因為他得知土耳其蘇丹“雷霆”巴耶濟德一世正率軍意圖圍攻拜占庭首都。幸運的是,早在皇帝趕到之前危機便已經解除了。來自中亞的帖木兒大汗在安卡拉戰役中決定性地擊敗了奧斯曼人,俘虜了巴耶濟德一世(後者大約一年後於帖木兒營中去世),奧斯曼人群龍無首,陷入了近20年的“大空位”時期,也給了拜占庭帝國一個喘息的機會。但是拜占庭並未充分利用這一千載難逢的時機,土耳其王子們經過20年爭鬥後,終於再次統一起來。1422年恢復元氣的奧斯曼土耳其蘇丹穆拉德二世又開始發動對君士坦丁堡的圍攻,不過由於王族內鬥以及帝國內部叛亂的傳聞,蘇丹不得不放棄計畫,提前收兵。
帖木兒的介入意外地使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延後了半個世紀,不過曼努埃爾二世從中獲得的進展並不多。他收復了色雷斯的幾座市鎮,並贏得了某個土耳其王子的友誼。雖然這是打擊東方的土耳其人,收復基督教失地的大好時機,然而,歐洲的基督徒聯合起來作戰的時代看來已一去不復返了。一支聯軍的出現,既需要時間,也需要共識,然而這兩者都是缺乏的。熱那亞人只關心其商業利益,缺乏長遠政策,而是企圖左右逢源,一方面向帖木兒派出大使示好,一方面出動艦隻將戰敗的土耳其將士從小亞細亞運回歐洲。威尼斯人將熱那亞視作最大威脅,要求其東方各殖民地長官嚴守中立。教廷正處於大分裂時期,兩位教皇互不相讓,自然也談不上領導基督徒了。西歐諸國依然對尼克波利斯的慘敗心有餘悸,加之英法重啟戰端,對干預東方事務也意興闌珊。匈牙利國王認為心頭大患已去,便將注意力都放在了角逐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寶座的遊戲中。——君士坦丁堡看上去已經高枕無憂了,誰還會關心它呢?
實際上,君士坦丁堡仍存在隱憂。不過,拋開這一點不談,城中的學術生活依然活躍。除去皇帝本人,此時學界的領袖為約瑟夫(Joseph Bryennius,神學院首席兼君士坦丁堡大學教授)。他培養了最後一批拜占庭優秀學者。此人學貫東西,幫助皇帝將西歐學術引入到了君士坦丁堡大學課程。儘管有諸多歷史恩怨,他與拜占庭學界對來自西方的學生依然敞開大門。教皇庇護二世(Pius II)曾寫道,在他的青年時代,義大利的知識份子均以在君士坦丁堡受過教育為榮耀。不過約瑟夫和曼努埃爾一樣,無法放棄拜占庭傳統,去轉而接受天主教神學。
另一位知名學者格彌斯托士•蔔列東[11](Georgius Gemistus Plethon),從君士坦丁堡移居至摩裡亞君主國首都米斯特拉。在這裡,他創辦了一所柏拉圖研究學會並出版了許多相關著作。他認為只有柏拉圖的哲學,可以重新喚醒希臘世界。他提出了不少政治、經濟甚至軍事上的主張,不過多數都失之空泛,難以施行。他的宗教觀點是柏拉圖主義、伊比鳩魯學說與瑣羅亞斯德主義的糅合。雖然表面上他也是個東正教徒,不過骨子裡卻有著古希臘異教氣息,例如,他把神拼寫作“宙斯”非耶穌。生前他的這些異端思想得到了寬容,不過在他去世及拜占庭首都陷落後,他的手稿落入了其朋友,時任君士坦丁堡大牧首的金納迪烏斯(Gennadius)手中,後者對其學說即著迷又感到恐懼,最後不情願地將他大部分著作付之一炬。
蔔列東的事例也說明了晚期東羅馬帝國發生了怎樣的變化。Hellene一詞從拜占庭帝國時期開始,漸漸專門用來指代希臘人,尤其強調其古希臘文化傳統的成分。雖然此時拜占庭已不復當年輝煌,不過在西方仍然擁有不少仰慕者,一些西方國家的人文主義者甚至自稱“希臘人”(HELLENES)。帝國的官方稱號依舊是“羅馬帝國”,不過在知識份子圈子中人們也不再稱呼自己是“羅馬人”(ROMAIOI)。這一風氣是從塞薩洛尼基發端的,該地居民尤其以自己的古希臘文化傳統自豪。14世紀末,甚至皇帝曼努埃爾也通常被稱作“希臘人的皇帝”而非“羅馬人的皇帝”。西方的宮廷也漸漸接受了這一稱呼。帝國最後的幾十年中,君士坦丁堡已經完全是一座希臘人的城市了。
曼努埃爾二世1423年退休,並於兩年後去世。他的摯友,土耳其蘇丹穆罕默德一世已經在4年前駕崩。新蘇丹穆拉德二世登基時,奧斯曼土耳其已經恢復元氣,國力強盛。希臘人一度對這位君主寄以厚望,認為他雖是穆斯林,但為人寬厚、公正,能夠與希臘人和睦相處。然而希望隨著1422年他對君士坦丁堡的圍攻而落空了。雖然對拜占庭首都的進攻未能得手,但他咄咄逼人的勢頭給希臘人造成了如此壓力,以至於曼努埃爾的第三子安德羅尼庫斯(Andronicus)在絕望中將帝國第二大城市塞薩洛尼基賣給了威尼斯人。然而即使威尼斯共和國也無力回天,這次交易甚至給了土耳其人藉口,塞薩洛尼基還是在1430年被奧斯曼帝國攻陷了。之後數年,穆拉德二世的擴張似乎停止了,不過這短暫的和平能持續多久呢?
曼努埃爾的長子,即約翰八世,確信只有求助西方才能挽救風雨飄搖的帝國,於是罔顧先帝的忠告,決心促成與羅馬教會的共融,因為他明白,只有羅馬教廷才具有足夠權威,將一盤散沙的西方天主教諸國號召起來,援救東方的基督教兄弟。此時,托大公會議運動(Conciliar Movement)之福,教皇終於從教會分裂中解脫出來(指1418年德國康斯坦茨會議選舉出馬丁五世教皇,結束了長期兩位教皇對立的時代,譯注。)。約翰深知只有通過某種“普世大公會議”才有可能促使國民接受兩大教會的再次統一,而此時,教皇也無法對這項動議斷然拒絕(因為教皇本人就是得益於大公會議而上臺的)。經過漫長談判,宗座猶金四世正式邀請拜占庭皇帝率代表團前往義大利進行會商。雖然約翰最初計畫在君士坦丁堡召開會議,不過最終還是妥協了。1438年拜占庭代表團前往義大利費拉拉參加會議,1439年會場移至佛羅倫斯(即費拉拉-佛羅倫斯大公會議,基督教第十七次大公會議。譯注。)。雙方代表進行了激烈地爭論。
這次會議的細節是冗長枯燥的。首先是關於“居先權”的認定。昔日基督教大公會議往往由羅馬皇帝主持,那麼今日的約翰八世是否應享有居先權?東正教大牧首與羅馬教皇孰高孰低?為此就花去了大量時間。會議原則要求以歷次大公會議認定的正典為基礎討論,表面上看與會主教們沐浴在聖靈的光芒下,群情激昂,然而熱烈的氣氛並不能彌補分歧。神父們時常互相批駁,甚至他們本身的論點也往往自相矛盾。語言上的障礙也是巨大的。某些拉丁語神學術語在希臘語中並無對應詞彙,同時,東西教會對於《聖經》正典的認定也存在分歧(例如,《聖經》舊約部分,天主教承認46卷,東正教承認48卷,多出的兩卷在天主教看來屬於“次經”。譯注。)。平心而論,在辯論中拉丁人表現略勝一籌。天主教代表團團結一致,精通辯術,並得到了教皇的幕後支持。而東正教代表團則是一盤散沙,何況還有一些優秀的主教拒絕赴會。不過拜占庭皇帝也帶來了幾名得力的神學家,包括尼西亞大主教特拉布宗的貝薩里翁[12]、以弗所大主教馬克(Mark Eugenicus)和基輔大主教伊斯多爾(Isidore)。代表團中甚至還包括幾位拜占庭知名的哲學家。東正教代表團本也被要求選出主要辯手參與討論,然而他們對此實際是陽奉陰違的——並沒有推出最強有力、最博學的人選。因為東正教會歷來的傳統是所有神父,甚至包括大牧首,在討論神學問題時一律平等。於是東正教的代表們就紛紛各自為戰了。而大牧首約瑟夫(為一保加利亞王子與希臘婦女的私生子)此時健康狀況不佳,難以發揮作用。皇帝約翰八世本人則忙於在辯論出現尷尬或冷場時息事寧人。整個拜占庭代表團顯得混亂不堪,並且多數神父都囊中羞澀,歸家心切。
最後,東西教會的共融還是被強制通過了。喬治•斯庫拉裡斯(George Scholarius)、喬治•阿米羅特斯(George Amiroutzes)與特拉布宗的喬治(George of Trebizond)三位學者因為對義大利神學家湯瑪斯•阿奎納的仰慕,而大力贊成聯合。另一位知名學者卜列東雖然對天主教神學並無好感,故未在最終檔上簽字——然而,他在佛羅倫斯受到了極佳款待,其在柏拉圖方面的研究備受義大利人推崇,因此,也就不好表示明確反對。大牧首約瑟夫之所以同意簽字,居然是因為翻譯的緣故,誤認為天主教的“和子說”與東正教教義並無本質區別——此後不久他就因病去世了。貝薩里翁等人則是出於對義大利文化的喜愛,以及將義大利、希臘文化整合的願望,而表示贊成。其餘絕大多數主教也簽字確認,當然一部分人是在皇帝的壓力甚至威脅下才這麼做的。唯一明確反對的只有以弗所的馬克。最終人們看到的決議,雖然也採納了某些東正教觀點、習俗,不過大體上還是天主教式的,而對於教皇與大公會議的關係,並沒有做詳細地約定。
簽字易,實踐難。當代表團返回新羅馬時,遭遇了民眾抗議的驚濤駭浪。一度備受尊敬的貝薩里翁,不得不離開拜占庭,前往義大利隱居,在那裡他意外地遇見了代表團同仁基輔大主教伊斯多爾,後者也被俄羅斯民眾放逐了。東正教大牧首則拒絕承認自己的簽字有效。在他去世後,皇帝一度沒有合適的牧首繼任人選。第一個候選人很快就逝世了,第二個人選格裡高利•瑪瑪斯(Gregory Mammas)雖然在1445年得到正式任命,卻被多數神職人員抵制,不得不放棄職位前往羅馬避難。而唯一沒有簽字的馬克則眾望所歸,名聲鵲起。當初贊成聯合的“三喬治”,一位心灰意冷避居義大利,一位成為了“拒統派”骨幹,一位甚至另闢蹊徑,嘗試在東方的穆斯林中尋找盟友。皇帝本人也動搖了,雖然未曾徹底放棄與西方聯合的理念,但在其母后海倫娜(Helena)的影響下,也不再強制推行。這一切都造成了拜占庭宗教、思想上的分崩離析。
不過本次大公會議的作用也不盡是負面的。一支新的十字軍被組建起來了(儘管有些不情願)。猶金教皇在1440年發出倡議,4年後,一支以匈牙利人為主的部隊在多瑙河組建起來。然而,教皇特使強迫聯軍統帥,特蘭西瓦尼亞總督匈雅提•亞諾什[13]撕毀與蘇丹訂立的神聖條約(從而背負駡名),並進一步在戰爭方略上對他多加掣肘。蘇丹穆拉德二世在黑海之濱的瓦爾納(Varna,今保加利亞第三大城市。譯注)不費吹灰之力,便擊敗了這群烏合之眾。最後一次試圖拯救拜占庭的十字軍也就此煙消雲散了。
於很多西方歷史學家而言,拜占庭人拒絕聯合的做法簡直是不可理喻,自掘墳墓。然而,廣大普通拜占庭人深受僧侶們的影響,以堅持信仰與傳統為榮,以背叛為恥。這是一個宗教氣息濃厚的時代。對多數希臘人來說,塵世的生活不過是彼岸生活的前奏,為了世俗世界的安定而犧牲信仰,玷污靈魂,這是絕不可接受的。即便國家滅亡,也可當做上帝對人間罪愆的懲罰,人們必須坦然以對。遠在帝國鼎盛時期,先知們早已傳言,羅馬的國祚不可能永恆持久。這種基督教的末世論深入人心,以至於人們相信,敵基督終會出現,末日審判無法避免。過去人們還堅信君士坦丁堡得到聖母瑪利亞的保佑,不會淪入異教徒之手,如今這份信念也動搖了。與西方“異端”教會聯合的觀念對他們而言既談不上靈魂的拯救,也無力扭轉世界毀滅的命運。
信徒們的觀點或許是偏執與幼稚的,然而,一些精明的政治家同樣對聯合疑慮重重。他們中的很多人預期西方國家不能,或不願,派出足夠強大的部隊與蘇丹的精銳之師抗衡。另一些人,尤其是宗教界人士,則擔心貿然聯合只會引發進一步的宗教分裂。當年十字軍的背信棄義還歷歷在目,如今很多在異教徒統治下的希臘人,僅僅是依靠教會這條紐帶與君士坦丁堡聯繫在一起,一旦試圖與西方教會共融,他們能否贊同是頗為可疑的。在高加索、多瑙河流域、俄羅斯也存在類似情況。東方的三大宗主教也明確表示反對(即亞歷山大宗主教、耶路撒冷宗主教、安條克宗主教,譯注。)。既然大部分東正教徒僅僅聽從大牧首的教誨而非拜占庭皇帝的訓令,又怎能強迫他們改變信仰以挽救帝國呢?俄羅斯人因為其世仇波蘭、斯堪的納維亞諸國信奉天主教,而對該教派尤其痛恨。1437年的一份檔表明,當時屬於東正教會大牧首領導的67位大主教中,僅有8位在拜占庭帝國有效統治區域內,另有7位處於摩利亞君主國範圍。換言之,一旦東正教會宣佈改弦易張,大牧首便有可能失去他四分之三的大主教。少數政治家甚至走的更遠。客觀地說,拜占庭已經積重難返。唯一保全東正教會並令希臘人民生活安樂的方法,或許就是接受土耳其人的奴役,其實,很多希臘人已經這麼做了。只有這樣,恐怕還有一線機會,令東正教民族積攢力量,東山再起,日後便可摘下異教徒的枷鎖。因此,當君士坦丁堡已經被土耳其大軍重重圍困之際,大公盧卡斯•諾塔拉斯(Lucas Notaras)竟然聲稱:“寧可在首都看到頭裹方巾的土耳其人統治,也不願看到頂著三層教冠的拉丁人統治。”(I would rather see a Muslim turban in the midst of the City than the Latin mitre)——此番言論也就不那麼顯得駭人聽聞了。
貝薩里翁為代表的拜占庭學者,在其“流放地”義大利如魚得水,備受尊敬,他們一方面盡力援助自己的同胞,一方面也對相形之下,君士坦丁堡的偏執愚昧感到痛心疾首。他們依然憧憬著與西方國家的聯合,相信義大利富有活力的文化能夠給古老的拜占庭一針強心劑。事後觀之,誰又能指責他們謬以千里呢?
約翰八世自義大利回國後又度過了鬱鬱寡歡的9年。他深愛的王后,特拉布宗的瑪利亞,病逝於一場瘟疫。他沒有子嗣,而他的兄弟多半在伯羅奔尼薩斯或色雷斯策劃者反對他的陰謀。他唯一信任的家庭成員只有其母后海倫娜,但後者卻與他政見不合。他盡可能地利用其機智與克制,維持帝國的穩定。他在財政上精打細算以至於節省出資金,整修了首都的城牆,後者很快便要面臨奧斯曼人的嚴峻考驗。當他與1448年10月31日駕崩時,或許對皇帝而言這真算是一種解脫吧。
注釋:
[1] 1071年,拜占庭羅曼努斯四世皇帝在曼奇克特會戰中慘敗於土耳其人,宣告了帝國喪失小亞細亞領土的開端。參見: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一》,鈕先鐘譯,桂林:廣西師大出版社,2004年,343-357頁。譯注。
[2] Adam of USK, Chronicon(ed.Thompson), p.57; Chronique du Réligieux de Saint-Denis(ed.Bellaguet), p.756. The best account of Manuel’s journey is given in Vasiliev, ‘The Journey of the Byzantine Emperor Manuel II Palaeologus in Westren Europe’(in Russian), Journal of the Ministry of Public Instruction, N.S., XXXIX,pp.41-78,260-304.See also Andreeva, ‘Zur Reise Manuel II Palaeologus nach West-Europa’,B.Z., XXXIV,pp.37-47. Halečki,‘Rome et Bazance en temps du grand Schisme d’Occident’,Collectio Theologica,XVIII,pp.514 ff. maintains that Manuel had an interview with Pope Boniface IX in 1402. The evidence seems insufficient;but Manuel did send envoys to the Pope in 1404;Adam of USK, op. cit. pp. 96-7.
[3] Theodore Metochites(1270-1332年),拜占庭政治家、作家、哲學家及藝術資助人,1305-1328年為皇帝安德洛尼卡二世重要顧問。譯注。
[4] 對於聖靈如何產生,基督教東西教會有不同理解。《尼西亞信經》中對此並無明確定義。羅馬天主教會秉承聖奧古斯都的觀點,認為聖靈由聖父、聖子共同產生,即術語“和子說”(Filioque)。而東方教會接受的為大馬士革的約翰(John Damascus)之理論,即聖靈由聖父產生,聖子、聖靈都借聖父而存在。是否接受“和子說”成為東西方教會在謀求統一過程中的重大神學分歧。譯注。
[5] 湯瑪斯•阿奎納(1225年-1274年3月7日),出生於義大利南部。中世紀經院哲學的哲學家和神學家,死後也被封為天使博士(天使聖師)或全能博士。他是自然神學最早的提倡者之一,也是湯瑪斯哲學學派的創立者,其著作成為天主教長期以來研究哲學的重要根據。他所撰寫的最知名作品為《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ca)。天主教教會認為他是歷史上最偉大的神學家,將其評為33位教會聖師之一。譯注。
[6] 約翰•坎塔庫震努斯(1292-1383),即拜占庭皇帝約翰六世,1347-1354年在位。他在安德羅尼庫斯三世統治時期,曾任帝國首相與軍隊總司令,被後人譽為帕列奧列格王朝最偉大政治家。安德羅尼庫斯三世去世後,他與其繼承人約翰五世就帝位繼承爆發內戰,史稱“兩約翰之戰”。坎塔庫震努斯依靠土耳其勢力,于內戰中一度佔據優勢,並成功加冕為皇帝,但最終因親土政策招致國內廣泛不滿,被首都民眾起義推翻,在修道院度過了餘生。這場內戰嚴重削弱了拜占庭帝國的實力。參見:陳志強:《拜占庭帝國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331-333頁。譯注。
[7] 斯蒂文在此用了一個術語apophatic(源於希臘語ἀπόφασις,本意為“否定”),其派生含義為“通過否定來證明”。東正教會神學有時也被稱作Apophatic theology(可理解為“反面神學”),即認為上帝不可捉摸,只能通過論述上帝不是什麼來探尋其存在。與之相對應的,則為Cataphatic theology(“通過肯定來證明”的神學)。由於東正教的這一特徵,其觀點相對傾向於神秘主義和不可知論。譯注。
 宗主教(希臘語:Πατριάρχης,拉丁語:Patriarcha)是基督教會中最高等級主教的頭銜(中文傳統上將東正教會的宗主教稱作“牧首”)。在基督教歷史早期,羅馬帝國境內五座重要城市(羅馬、君士坦丁堡、安條克、亞歷山大、耶路撒冷)是基督教的主要教區,該地主教地位崇高,擁有最古老的宗主教頭銜。上述五地合稱五大宗主教區(Pentarchy),按歷史榮譽,其主教排名先後如下:西方宗主教(即羅馬教宗),君士坦丁堡、新羅馬大主教和普世牧首,亞歷山大和全非洲牧首,大安條克和全東方希臘教會牧首,耶路撒冷聖城和全巴勒斯坦牧首。理論上,羅馬教皇作為聖彼得繼承人,享有“首席”地位,但依據東正教傳統,西方宗主教並無逾越其他主教的特權。2006年,“西方宗主教”這一頭銜被現任教皇本篤十六世於官方檔中刪除。譯注。 宗主教(希臘語:Πατριάρχης,拉丁語:Patriarcha)是基督教會中最高等級主教的頭銜(中文傳統上將東正教會的宗主教稱作“牧首”)。在基督教歷史早期,羅馬帝國境內五座重要城市(羅馬、君士坦丁堡、安條克、亞歷山大、耶路撒冷)是基督教的主要教區,該地主教地位崇高,擁有最古老的宗主教頭銜。上述五地合稱五大宗主教區(Pentarchy),按歷史榮譽,其主教排名先後如下:西方宗主教(即羅馬教宗),君士坦丁堡、新羅馬大主教和普世牧首,亞歷山大和全非洲牧首,大安條克和全東方希臘教會牧首,耶路撒冷聖城和全巴勒斯坦牧首。理論上,羅馬教皇作為聖彼得繼承人,享有“首席”地位,但依據東正教傳統,西方宗主教並無逾越其他主教的特權。2006年,“西方宗主教”這一頭銜被現任教皇本篤十六世於官方檔中刪除。譯注。
[9] 曼努埃爾二世之父在位期間王室成員曾爆發內戰,而曼努埃爾二世本人則相對與皇族關係和睦。不過約翰七世僅在位一年便撒手人寰,曼努埃爾二世隨後登基。譯注。
[10] 天主教大分裂時期,1378-1417年。1377年,教皇格裡高利十一世(Grégoire XI)把教廷由法國阿維尼翁遷回義大利羅馬,他去世後,樞機團分別選出一名義大利人和一名法國人為繼承者,即烏爾班六世(Urban VI) 與克雷芒七世(Clément VII)。兩位教皇互不承認,甚至開除彼此教籍。於是在法國和義大利出現了兩個教廷。直到1418年德國康斯坦茨(Konstanz)召開的大公會議終於選出了各方一致認可的教宗馬丁五世(Martin V)才宣告這一分裂結束。先前提到1396年的十字軍居然是由兩位敵對的教皇各自派出,當年的混亂狀況可見一斑。譯注。
[11] 格彌斯托士•蔔列東(約1355年-1452年),拜占庭著名柏拉圖主義哲學家,也是在西方推動復興古希臘學術的先驅。其學說在15世紀的義大利影響很大。譯注。
[12] 貝薩里翁 (Basilios Bessarion, 姓名希臘文拼寫為Βασίλειος Βησσαρίων,1403-1472年),文藝復興時期著名拜占廷人文主義學者。他出生于特拉布宗,青年時代遠赴君士坦丁堡求學,師從蔔列東。1437年被拜占庭皇帝任命為尼西亞大主教(Metropolitan of Nicaea),並隨後參加了費拉拉-佛羅倫斯大公會議。此後長期定居義大利,著書立說,贊助學者,並于拜占庭滅亡後盡力援助逃難的希臘同胞。1455年一度被作為教皇候選人之一,1463-1472年任天主教會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貝薩里翁生前收藏有大量希臘文手抄本,1468年,他將其捐贈與威尼斯議會,今收藏於著名的威尼斯聖馬可國家圖書館(The Biblioteca Nazionale Marciana)。譯注。
[13] 匈雅提•亞諾什(匈牙利語為Hunyadi János,英文一般拼寫為John Hunyadi,1407-1456年),曾任特蘭西瓦尼亞總督、匈牙利王國攝政,為匈牙利對抗土耳其之名將。一生最輝煌戰績為1456年率軍于貝爾格勒圍城戰中大敗蘇丹穆罕穆德二世,但本人也於戰後不久因感染鼠疫病逝。其次子匈雅提•馬加什在1458年加冕為匈牙利國王。譯注。
|


